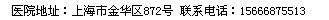您的当前位置:寡趣症 > 寡趣病因 > 两个女人争老公,笑的脸抽筋
两个女人争老公,笑的脸抽筋
点赞+转发
点手指下面看更精彩内容原创
静夜幽幽,皎月寂照,咏菊小阁内却慌成一团。 「小姐,药拿来啦!快,快生服下。」喜菊皱着眉头服侍湘柔服下一小瓶肠胃散。 湘柔乖乖地吃药,已胃疼得无力多言一句。 喜业气嘟嘟的,好似受了很大冤屈。「虽说咱们做下人的不该批评主子,可喜棠真不知夫人是怎麽想的:小姐可还是个黄花大闺女呢!怎可同那个江湖郎中孤男寡女的在房里练琴:这事若传出去,将来小姐怎麽嫁入呀?」 之前喜棠口口声声夸赞的「名医」这时已成了「江湖郎中」湘柔嘴里虽不说,全里可是很明白二娘的盘算。但她既然决心回报爹爹,使再也无一丝为自己打算的想法了。 湘柔数了一声,抬眼望向窗外一轮皎白明月,幽幽喃语。「咱们生为女子,终生能企盼的便只有嫁入了吗?嫁得好还罢了,若所嫁非人,岂止贻误终身?」眉的丽颜上有一丝落寞。 喜棠、喜菊对瞧一眼,皆面有忧色。 喜菊道:「小姐,你又说些咱们听了不懂的话啦,可别是受了姨姑娘影响,净往些古里古怪的念头上钻!」 湘柔微微一笑,也不争论,伸了伸懒腰。「啊,好困哪;你们两女也累了一天,快些回房休息去吧。」不等两人回话,已面朝里侧躺下。 喜棠、喜菊面面相觑,无可奈何地咕侬两声,也只得闭上嘴巴乖乖离去。 睡梦中仍隐隐感到胃部作疼┅申吟了声翻过身子,不适的感觉非但不减反倒加剧。 湘柔迷迷糊糊地,抱着肚子痛苦地睁开眼┃她在作梦吗? 不然,为什麽会看到 邵风!? 湘柔猛地自床上坐起,一惊之下,险些尖叫出声!幸而他有先见之明,早一步 住她的嘴。 「噤声!不然我又得点你哑穴。」他靠近湘柔耳畔,呼出热息。她十分厌恶地摇头,却心悸於他迫近的男性气味。 「保证不叫喊?」 她肯定地猛点头,肌肤上已鼓起一粒粒的疙痞。 他低笑,随即放手。 「我┅┅我在作梦吗?」湘柔睁圆了尚且迷蒙的眸子,茫然地揪住他。虽早知他行事不能以常理度之,但夜半闯入她的闺房毕竟匪夷所思。 他擒笑。「你说是梦,也成。」 这自然不是梦了。可三更半夜的,难道他是来向她道晚安的? 「你在想,我深更夜探所为何来,是不?」他眸底敛着诡笑。 湘柔心神恍惚的说了傻话:「难不成,你是来同我道晚安的?」 他忍不住仰首无声而笑这未晓人事的黄花闺女! 「你----不怕我?」他低垂眼脸,戏谑似地讽笑她的青涩。 「怕你?」她眨眨眼,水漾随瞳眸闪呀闪地。「嗯┅┅某些时候┅┅是有些怕的!」微微红了脸,她垂首,呐呐说道。 「某些时候?」他一指托高她的下颚,不容她闪躲。「例如?」 湘柔小脸条地刷红,连裸出的一小截粉白颈子霎时间也染成粉红色泽。「好似┅,好似那日在┅┅在竹舍。」她两手揪着自个儿胸口的衣棠,不懂何以每回同他说话,总像自己做了什麽亏心事似的,好好的一句话总说得结结巴巴。 他唇色邪扬。「是吗?」 他眸光转深,似笑非笑地瞧着她瞬间胀红的白皙肌肤,几绺松散的乌丝垂落在艳红的颊畔,这模样儿┅┅是撩人的。 「胃还疼吗?」他哑着嗓子低问。 她睁圆眼。「你怎知我胃疼?」 他低笑。「我是个大夫。」 若非她脸儿已红得不能再红,相信还会再添上一层羞赧的颜色;她真是问了傻话! 「如何?当真还疼?」 「睡前吃了药,比起稍早好些了。」羞怯的眸子,泛着水灵灵清光。 他动情地伸手为她拂开颊边的乱发。「那麽,方才我听见的申吟声是怎反回出忑?」动作细拭温柔。 「啊?」她迷惑於他轻柔的指,逗惹地摩挲耳後那片敏感的嫩肤┅┅她有些心神荡漾。「什麽┅┅什麽申吟?」 他低笑,双唇押近她耳迸道:「你睡着时还喊疼,忘了吗?」醇厚的嗓音融揉魅惑。 「是┅┅是吗?我不记得了┅┅」她有些想笑:只觉得他热热的气息喷拂在她耳後好痒,惹得她直往里缩,忙着躲开他,以免当真笑出声来。 邵风不悦地伸手按住她的小腹,考虑着是否要用强硬点的手段。 她一愣,两眼瞪住他搁在自个儿小腹上的大手。「没关系┅┅老毛病罢了┅┅忍一忍就过去┅┅」 虽说在交易之时,她便早有,「觉悟」,但这「觉悟」的方法,她可是半点儿也不懂的。通常也只有即将出阁的闺女,才会被授以这方面的常识,因此她对男女之事的「认识」,便只有一直停留在那日两人於竹舍的接触。 「手伸出来。」他命令。 「啊?」虽不知他是何用意,她还是乖乖伸出双手。 握住她冰凉的心手,他眉头微皱,一言不发地分别搭了她两腕的脉搏。 「不必为我费神了,我时常胃疼的,只要忍一忍便没事┅┅」湘柔因他握着自己的手而有些紧张。 「脱下衣棠。」邵风头也不抬地说着。 「啊?」她再次瞪大眼。 「我说----脱下衣棠。」他邪笑,懒懒地说道。 「脱┅┅脱下衣棠?」 「啊?」她再次瞪大眼。 「脱┅脱下衣裳」 「没错。」见她默默地愣住,他嘲弄地撇撇唇。「还不动手?莫非要我代劳吗?」 湘柔一脸惊惧的欲往床角缩,双手挣脱他的掌握而死命的拉紧自己的衣襟。无论如何她是没有勇气在男人面前宽衣解带的,现在他瞧见自己只着薄衫的模样,只是不合礼数了,她只觉得两颊烧得火热,心泺剧烈几乎要突出胸口。 瞧着她羞怯的模样儿,他眸光忽尔深浓,猿臂一伸,将她扯入怀里。 三、两下褪下她的衣肢;一片雪白的扮背映着苦皎亮的月色呈现在他的眼前。怀里的人儿哆嗦的厉害。邵风黑眸转浓,狠心的漠视湘柔楚楚可怜的凝眸┅┅ 然後她便觉的前一黑,失去了知觉。 难道真的是作梦? 可是自己身上由他两手揉按的地方却又好疼! 面朝床内侧散开中衣和里衣前襟,松解抹胸的带子,检查自个儿的身子┅┅昨夜她果然不是作梦!只见自个儿胸前和小腹,依稀烙着两道手印子的瘀痕!奇怪的是两道手印的中间有两枚殷红如血的小圆点。 瞧着那两道手印覆盖的面积,她连耳根子也烧红了。原来失身」便是这麽回事事吗?那麽往後每回都要这麽疼了? 思及此,她立刻轻斥自己;但她又忍不住想,是不是因为她昨夜晕过去,一时惹恼了他,所以他也不唤醒她便离去┅┅兀自发着呆,忽听得喜棠、喜菊两个丫头的说话声由远至近,一路朝她房里来,慌得她乱手乱脚的胡乱拉拢衣装,闭紧了眼,假做酣睡。 「小姐,该醒啦!快生起来梳洗、用早膳,还得同老爷请安去呢!」喜菊走近床榻来唤她,喜棠则忙着推开小阁的窗子。 湘柔应声睁开眼,小伸一下懒腰,徐徐自床上坐起,正要下床,忽听得喜棠「噫」了一声。「怪了,我明明记得昨儿个这窗是我给虚掩上的,怎地今早却掩得实了?」 湘柔的心「怦」地跳了一下,连忙道:「是昨儿个夜里我给冷醒了,便起来把窗户掩实。」 喜棠哦了声,不疑有它。湘柔暗暗吁了口气。 想来昨夜他定是自这窗子进出了。 往忆梅轩的路上,须经过明心阁,湘柔知道邵风是家里的上宾,定是安排住在明心阁内,是以经过时不免瞧上两眼:全头扑跳得厉害,脸儿已先红了。不知他昨晚是否当真恼她晕过去?他气自个儿是不要紧的,可别因此後悔同地做了这笔「买卖」,误了爹爹的痛┅┅湘柔正胡思乱想,不觉已到了忆梅轩,自椰子尉房里传出极浓的煎药味。 「爹爹,今儿个觉得怎样?」进了柳子尉房里,湘柔接过冬梅手里的药汤,坐在塌下亲手喂服。柳子尉今日气色不错,因病而给折腾得焦黄憔悴的脸甚至露出一丝笑容。 「昨日那位新来的邵大夫果然高明,不同以往那帮庸医,昨儿个也不过在我身上扎了几针,夜里这病发作时的阚痛竟减了大半。」 「真是如此?」湘柔好生安慰,自己总算不是白白牺牲。「若爹爹再让邵大夫施几回针,病体便要全好了!」 柳子尉呵呵笑,甚是慰怀。邵大夫真是神医,爹这病若当真全好,咱们可得好好答谢他,邵大夫有何要求,即便是难如登天,老夫也得给他排妥!」 这话说中湘柔的心病,她脸上又是一红,垂下了脸,嗯了一扛,却答不上话。 柳子尉病况稍有起色,忽然想到一事。「柔儿,你今年也已有十七、八岁了吧?」 湘柔抬起脸,不明白爹爹此间是何用意。「柔儿今年二十了。」 「二十了?」柳子尉一某,脸上一片茫然。 湘柔无语,知道爹爹已病得糊涂了!心里不禁有些哀伤。 「你已经二十了!」柳子尉仍是满脸震惊。「你二娘想必替你许了人家了。」 「二娘,她┅┅她自爹爹病後一肩挑起家里的生意,多亏二娘把爹爹的生意经营得好生兴旺。可二娘终归是女子,成日打理商号已是分身乏术,自是┅┅自是无暇顾及柔儿的婚嫁。「这番话说得再婉转不过,尽将自己的委屈都掩藏不提,反倒夸薛宝宝的好处。湘柔的用意是希望柳子尉宽心。 「原来是这样┅┅」柳子尉自是相信了。沈吟片刻道:「等我这病再好些,便亲自作主,替你挑一门亲事。只怕到时登门来求亲的人要挤坏咱们柳家大门了!」 湘柔闻言不语,只是浅笑,可心里却是忧虑的。她自然希望爹爹的痛早日康复,但今生她却是不能嫁入了。 就算不提,她已将自己「卖」给邵风的事,经过了昨夜她已非清白之身,如何还能嫁入?况且如今在她心里,再也容不下另一名男子,即便是让其他男人瞧自己一眼都觉得不净。 思及此,湘柔愈是忧挹了。 他已在自个儿心底有了这般影响力了吗?如此一来,就算自己不能嫁他,也要如此为他牵 挂羁绊一生吗? 莫怪菀姨要她不可理睬,下可信任,甚至终生也别见男子;或者菀姨此言确是有道理的┅┅离开忆梅轩,一路上湘柔眉轻颦。有了「惦念」,已然不能再同以往一般心如止水。这,是因何而生的呢? 想起自己与邵风之间的「交易」┅┅清楚他对自己并无怜爱,待他厌腻了,她的命运又将如何? 「小姐,方才你在爷房里真不该替夫人掩饰的!幸而老爷舟应要替你作主挑二门亲事,否则你的终身大专又要被耽误了。」喜菊随湘柔回往咏菊小阁的路上,嘀嘀咕咕的抱怨。 湘柔淡淡微笑,不置一言地任喜菊喳呼个没完没了,只管想着自己的心事。 「柔表妹┅┅」 一名模样儿斯文,身着宝蓝色缎袍的男子立在小径旁唤住湘柔。 喜菊低呼:「是表少爷。」当下跟薛子平福个身,恭恭敬敬地道了声:「表少爷好。」 薛子平颔首,见湘柔正要欠身,忙上前一步意欲扶住她,湘柔一惊,猛地往後踉跄了几步。 这一来,薛子平自是甚为尴尬,全底限起自个儿唐突,深怕表妹就此瞧不起自己。「柔表妹┅┅我┅┅」却是不知如何开口解围,顿时又恼又悔,甚是狼狈卜他方才乍见柔表妹,如此巧遇令他又惊又喜,尾随踌躇了良久,才鼓足勇气上前同表妹说话,谁知一见到表妹便出丑失态,教他怎能不恨自己无用! 湘柔低低敛下双眸,轻问道:「表哥┅┅有事吗?」未料到曾在此遇见薛子平,更不想他竟会伸手扶自己,她一惊之下明显的退拒定是教他难堪了。 「我┅┅我┅┅」 薛子平嗫嚅了半天,连喜菊也瞧不下去了。喜菊心底是希望这位表少爷能中意小姐的!想走这小径左右四下无人,又是野外空旷地方,留下表少爷和小姐二人想是无妨的,说不准表少爷有啥悄悄话要同小姐说理!她眼珠子一转,当下便有了计谋。 「小姐,你和衷少爷说话,我可得先回小阁去了;喜棠还等着我回去帮忙打扫屋子呢!」说罢便开溜了,没给湘柔回答的机会。 「喜菊┅┅」 湘柔徒劳叫唤,又不能无礼地撇下薛子平离去,只得勉为其难地留下,一时却又找不出话题,场面好生尴尬。 「柔表妹,方才┅┅是我唐突了,你千万不要见怪,我平常不是这样的!」总算教他找回一点理智,想到该先解释。 「不要紧的,方才湘柔也有不对┅┅」 「不不,总之是我不好,与你是没有关系的!」 湘柔不再和他争不好之名。「表哥,您唤住湘柔是否有事吩咐?」 「我┅┅」薛子平胀红心。「今早,我听姑母说,那新来的邵大夫诘表妹相助为姑爹治病;当真┅┅有其事吗?」 「二娘说的是事实。」 薛子平听湘柔亲口印证果有此事,霎时间忧急如焚。「那邵大夫是个轻浮浪子!他要求你配合之事违害礼法,分明是图谋轻薄,表妹你的名节要紧,此事不妥,万万不可答应!」他言语激动。 「昨晚我已答应邵大夫,二娘也允许了。」湘柔一脸平静。若非不愿失礼,她根本没有解释的必要。 薛子平一愣,继而愁恼得连声音也颤抖了。 「表妹┅┅你怎可答应此事!这事┅┅这攸关你的清白名节哪!」 湘柔抬起清亮双眸,淡然而笑。 「表表费心了;湘柔答应此事,早已将名节二字置之度外,一心以爸爸的安危为系,他人若要试毁,湘柔不无怨言。」 薛子平难以相信外表如此纤弱的女子,竟有勇气无视世俗的礼教批判,率心而为。 「可是┅┅表妹┅┅你这麽做┅┅对你将来出阁,会有很大的阻碍┅┅」 「婚姻之事乃缘分,强求不得;别人若要介意,那也是无法可施的事」不需要告诉薛子平,她原无嫁人的打算。 「我┅┅我不介意!!」薛子平突然喊道。 话一出口,薛子平便知道自己又唐突了:但这本就是他自昨晚见到湘柔後,心中辗转酝酿的情思,此时虽贸然说出口,而他却是不後悔的。 湘柔却教他这番表白弄得不知所措,别开了眼轻蹙起秀眉。「时候不早了,喜棠、喜菊已等着我用午膳,湘柔得告辞。」微一颔首,她加快脚步离去。 薛子平不敢迈步去追,只是凝凝望湘柔的倩影出神,思及方才的冲动,心底又是不安,又是甜蜜;待想到邵风蓄意轻薄的要求,又觉得可恼、可恨,不由得苦苦寻思,该如何解救纯良的表妹,不致教那狂徒给欺侮了。 呆呆杵在原地苦思了许久,终於让他想出一备两全其美的法子,薛子平不由得脸上露出笑容,纠拧的眉头总算松了开来。午后,咏菊小阁内只剩湘柔一人独守:午时过後不久,薛宝宝即差来春菊支走棠、菊两丫头,吩咐她们两人上菊苑帮忙。 湘柔独坐案前抚琴,她在等「他」到来。 邵风无声无息地潜近她身畔,捞起她肩上一缕长发,凑近鼻端嗅闻。 「在等我吗?」 蓦然止住了琴声,她脸儿又红了。 她知道他会来,也确是在等他,可一见了他,湘柔不由得思及昨夜,连忙低低垂下脸。 她不敢瞧他。 他附在她耳畔低语,瞧见她垂下脸後袒露出的一截白後颈竟也染上霞泽。 她悄悄悃眼偷觑他┅┅这样近的距离瞧他┅┅他真是个好看的男人。她这辈子虽没见过几个男子,可是他俊得教她移不开目光,但是他最吸引人的还是他那满满的自信┅┅或者该说是任为吧!特别是两人独处时他那任意而为的狂态更形放肆。 「如何?满意吗?」邵风唇角勾出邪笑,知道她正在偷瞧自己。 她羞怯地垂下眼,却教他扣住下颚,强抬起它的小脸迫使她面对他。 「现在只有我们两人独处,不必避嫌与害羞。」他刻意提醒她,深瞳里带着邪魅。 「你是来传授我医谱口诀的吧?」湘柔不知如何回答,只好顾左右而言它了。 他微眯起眼。「你不好奇昨夜发生何事?」 他的直言令湘柔大为羞窘。 她该好奇吗?不就是「那回事」? 「昨夜┅┅我晕了过去,你┅┅」她怯怯地问,羞弱的气质如水般娇怜。 「你身子纤弱,又不懂武艺,会疼晕过去是理所当然。」他幽邪的瞳眸潋出诡光。 「这麽说┅┅你不生气?」她声若蚊蚋没敢瞧他。 他挑眉。「我为何要生气。」慵懒的语调隐杂不易辨识的撩戏。 湘柔轻吁口气,算是安心了,可及昨夜那疼痛 「既然你不生我的气。那麽,我可否┅┅可否你一个问题?」粉嫩的阋腮泛成一片媚人的绯色。 他探手抚她红彻的娇颜。「说。」 湘柔敛下眼睫,实在觉得难以启齿。「是不是┅┅是不是每回┅┅都是那麽疼┅┅」好好一句话又让她说得七零八落。 邵风的反应是仰首大笑。 湘柔羞窘得无地自容,别过了脸,眼圈儿都泛红了!他可是笑她不知耻? 好不容易他终於止住笑,唇角犹挂着一抹兴味。 「小傻瓜,昨晚并非你的初夜。」他使坏的阖意将重音放在「初夜」二字上。 湘柔呆呆地揪住他,为他的话一时傻住了。「可┅┅我们┅┅你┅┅昨晚你分明要我脱了衣棠┅┅」 邵风唇角邪扬。「过几日,你便会明白。」回答得颇为不纯良,意在暗示她住嘴。总之这回事「说」不明白。 果然湘柔听懂他言下之意,条地又胀红脸,不好再问。 「昨夜我察觉你脉象有异,之所以要你脱下衣棠,是为了印证猜测。之後我以自身内力导引你的内息,果见你身上两处穴道上浮现出两枚殷红的血点。」他道。 原来如此。而她竟误以为他┅┅真是羞死人了! 声音痛哑的说:「这样容易脸红┅┅可知昨夜你连身子也霞红,我险些要分辨不出那两枚血点了。」他兀自撩戏她,似乎以此为趣。 「我┅┅当真病了吗?」她笨拙地顾左右而言它。 「是病,」他语调佣懒地略略谜紧星眸。「也可说不是病」 「我不懂?」 「你身中剧毒。」他深深端凝她,黝黑的眸光凝敛深沈。 湘柔惊讶地失了言语。 「不相信我的话?」 「不,只是不明白┅┅怎会有人对我下毒?」她心中的诧异远胜於不信。 「你所中剧毒是『碧凝香』。」他淡淡道出,凝视她的眸光却无比犀利。 「『碧凝香』?」轻蹙黛眉,确定自机压根儿未听说过这三个字。「这毒┅┅十分狠险吗?」 「确是极险,」他笑容抹上邪味。「只不过要引出『碧凝香』之毒尚需一味毒引。」放沈的语调释放出幽深的情色。 「毒引?」药引倒是听过的,可毒引就教她不明白了。「这毒需以何物为引?」单纯如她,是分辨不出他语谛中的危险的。 他笑得有深意,却不直接作答。「我俩老是离题,所谈皆非正事。」 这话提醒了湘柔,她竟忘了他上咏菊小阁来,主要是为了传授她医谱口诀好替爹爹治病 「我真该死,咱们要开始练琴了吗?」他既不欲谈,想来必有把握解自己身上之毒,故而也毋需追根究柢了。 毕竟爹爹之事才是首要的。 他自怀中取出一卷琴谱递给湘柔。「你先练习数遍,待熟稔後我再传你口诀。」他回复淡冷,瞬间已敛去撩戏的狂态。 接过琴谱,湘柔凝心演练起来。这琴谱用韵极险,往往在极高之处忽转低调,若非湘柔在琴艺上有超人的修为只怕绝不能弹奏。饶是如此,费尽一下午的时光竟是一遍也不能练成┅┅ 夜色深沈,还天星辰亦隐蔽无光。 杭州城外十里处,一片杂树林里两道阒黑的影子「少爷。」苍老的声音发自一身形粗壮的黑衣人之口;此人毛发灰白叁羞,一张脸生得悲郁沧桑,说话中气不足与体形甚不相配。 另一名颀长伟岸的黑衣人双手负背道:「你以千里香唤我,师父有事吩咐?」 「是。」老者对年轻的黑衣人态度甚为恭敬。「李先生要我转告少爷,毒手药仙已重出江湖,日前曾在开封一带现身。」 「师父的意思是?」 「待咱们完成复仇大事───」提及仇恨,老者面孔忿然扭曲,使得原已不善的面色更形丑怪。「李先生希望少爷立即上开封查明此事。」 年青的黑衣人-----邵风沈吟半晌。「我明白了。」 「少爷----」老者欲言又止,似有犹豫。 「有话直说无妨。」 「是。老奴以为┅┅」踌躇片刻,老者终於道出;「少爷何不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当仇家先下毒戕害,後又上门杀人;少爷┅┅」 「你认为我处置的方式不当?」邵风淡淡说道。 「老奴只是以为,少爷对待仇敌的方式┅┅太仁慈了些。」恭谨的语调,透出他决心出言进谏时,心怀的畏惧。 「四叔,咱们如今要对付的,是怎样的敌人?」邵风面无表情,代表活是他最冷血无情的时刻。 朱四臣虽不知邵风此间有何用意,仍然回答:「是一名年轻姑娘。」 「嗯。她可懂武艺,可会用毒?」 朱四臣呐呐说道。「是个平凡姑娘。不懂武艺,不会用毒。」 邵风唇角勾出残冷酷笑。「那麽,对付这样一名闺阁弱女,以毒残戕、手刃其身,难道会比押亵玩弄,诱其失节,更能深创对方吗?」无波的音调冷得不带一丝人味。 朱四臣张大了口,难以反驳,却真正明白少爷复仇之心切,只在自己之上;少爷报复仇人的手段确是比自己残酷十倍。 「可是少爷,这似乎┅┅似乎┅┅」 「四叔,方才你说,不该对敌人心怀仁慈的。」邵风冷言堵住朱四臣的嘴。 朱四臣一时显得局促不安。「是啊,对付敌人是不该仁慈,可是┅┅少爷您这麽做似乎┅┅不妥┅┅」揣着志忑,他勉力压抑忧惧硬着头皮冒犯森冷的少主。 邵风骤然狂笑。「四叔,你是想说──邵风如此行迳形同采花淫徒吧!」 朱四臣垂首,讪讪无话。尽管畏惧主子的气势,却是一心护主的,不则他大可选择沈默明哲保身。 邵风狂态未去,俊冷的侧面复添三分邪谑。「当年我眼见爹娘横死於眼前,清啸庄十馀条人命死无全尸,遍地血流成河便已明白所谓礼教道德不过是用来粉饰鄙意劣谋的面具!邵风在报仇这件事上不耐烦做伪君子,宁愿当真小人,拂逆我性随天下人同流合污!」说罢仰首对月狂笑,瘦削的俊颜一变狂佞的嗜血。 「少爷┅┅」 朱四臣骇然哑口,已不知该当何言,内心惶惶不安。 睡梦中,湘柔直觉地睁开眼来,凝入一双黑子夜的漆眸。 「你┅┅」挣扎着自床榻上坐起「噤声。」 邵风示意湘柔侧卧於床榻上,面向里侧,他亦盘坐於床上,一手横置於湘柔背心的穴道上方,一股至暖的内力立时源源不绝地注入湘柔桓内。 约莫半盏茶时分过去,直蒸得湘柔佬热难当,通体发红,香汗淋漓,邵风方才收掌,舒了口气调匀内息。 「脱下衣棠。」他命令,并探手人怀中掏出一方紫金檀盒,「嗤」的一声弹开盒盖。 这回湘柔不再惊惶失措,知道他今夜再来必是为自己治玻可饶是明白,还是万分尴尬地背向他自床上坐起,面朝床里侧,颤着手羞赧地除下衣衫…… 胯下的阚痛让他皱起眉头。咽下喉头的乾涩,他翻身下床。 「你要走了?」湘柔疲乏地卧伏在床上,芙白的面颊上染着欢爱的潮红,美丽得犹如出水的仙子。 「抱歉不能陪你到天亮,否则明日我俩怕要被当作奸夫淫妇,五花大绑游街示众了。」他凝聚意志忽略下腹的阚痛,气息粗重的说笑。他不得不走,再待下去他 该死!她不该以那双水澄的大眼柔柔地凝娣他日他眸光幽沈,黑瞳澈出冷光,眉宇间流泄出阴郁的冷酷。「乖乖歇息,咱们还有无数个夜晚。」 湘柔柔顺的微笑,她累得无暇再多想,更意会不到他眉宇间悠忽的阴沈。 邵风走了。房里头又只剩湘柔一人及冷清清的夜。 湘柔知道,方才地对自己做的是她得偿付的「代价」。可虽名之为「代价」,她却尝到了前所未有的欢快。他,可也如她方才一般得到快乐了?如果是,何以他要急着离去? 她在胡思乱想些什麽?这不过是场交易罢了!但┅┅她道自己方才心中压根儿未想到「交易」二字,是自然而然的想将自己给他┅┅天,她心窝儿烧着的是什麽?明知道自己有法是不知耻的,可┅┅不----她不能再多想了。 不该再多想了呵┃他要的不过是几晌欢快,一开始他使说明了的。 霎时间,两颗泪珠儿滚下湘柔的颊┅┅月儿由盈转亏,眨眼菊月将逝,天候逐渐转冷。 「小姐,你也不必再练琴了。眼看着老爷一日好过一日,再不多久便要复原了,你不同邵大夫练琴也不妨碍了。」喜菊手上摺着几件冬衣,是预备天再冷些便可让湘柔穿上的。 「不成,这琴还是得练下去的。就算爹爹现下病好了,我练成了医谱,也可日日演奏给爹爹听,为爹爹延年益寿,这功夫是不能搁下的。」喝口甘润的菊茶,湘柔挥毫临帖。这时有菊丫头在,她是不能抚琴的。 喜菊软口气,也不多费唇舌了。这个把月来她和喜棠早说破了嘴,就是不能劝得小姐罢手不练那劳什子医谱。现下一日日过去,就是此刻能劝得小姐放手,也已无甚作用了。 如今这府里众人早已知道小姐日日同那大夫关在房中练琴,大夥儿虽然明里不说,暗里却是不乾不净的说些谣言中伤,也许这事儿也早传出府外,或者现在杭州城里人人都知道。 她暗自又软了口气,随即将摺好的大衣一件件收入次箱。「小姐,我到後头瞧瞧喜棠去,顺道施些花肥。」 「去吧,别理我,自管忙你的。」说话时也不抬首,专心临帖。 喜菊去了没多久,门前叉有动静。 「怎麽啦,忘了什麽事又转回屋里来了?」湘柔不经意地抬眼一旁,却见到门外站着的是一脸尴尬的薛子平。「表哥?」 「柔表妹。」薛子平脸上有些微红,起初尚有忸怩,但旋即现出一股决心。「表妹,我有些话想同你说,可不可以┅┅进你的屋里谈?」 微一冷吟,湘柔拦下手中毫笔。「咱们到前院谈吧,那儿有个小亭子,也凉爽些。」说着起身步田屋外。 薛子平亦步亦趋地跟在湘柔身边。对於表妹提议到亭子里谈话,虽觉得於礼当然,哥心下不免有些黯然。心想若是毓表妹,定不等他开口早已请他入屋内,可见柔表妹对自己客气疏远得多。 两人没走没几步已到一所青竹搭的小亭,亭子虽然简陋了些朴素中倒很有清凉之味,让人身心舒畅。亭子的栏杆上钉了一竹牌,上面刻着「问心」二字。 「表妹┅┅」薛子平迟疑耍如何开口。「近日以来姑爷的痛渐有起色,我想┅┅你应该不须再跟邵大夫练琴,我┅┅」 「表哥,这事莫再提。只要对爹爹有益,不管用不用得上,湘柔都要试试。」 「可是表妹,你终究是要嫁人的──」 「表哥,记得我们上回已就这事讨论过了,不是吗?」湘柔淡淡一笑。「婚姻乃缘分,同我练不练琴是无相干的。」 薛子平磨拢眉头。「表妹,你似乎不甚在意自己的婚事?」 「亦非不在意,而是在意不得。」目光远眺远处一池碧波,湘柔轻轻的说:「做人便是这样,在意太多亦不一定能尽如己意,何苦招惹烦恼?」 「话是不错┅┅」薛子平眉头皱得更深。 表妹的思想远不同一般女子,虽情逸高卓,但一个姑娘家有这样的见地似非善兆。 「表哥既然也同意,就不须再为湘柔多费心了。」收回眸光,她朝薛子平浅浅微笑。 「不,只要有关表妹的事,我是不可能不关心的。」他顽固道。 湘柔轻叹了一口气。「您这又是何苦呢?方才我已说过了,做人实无须多惹烦恼┅┅」 「但表妹你并非我的烦恼-----将来你可是子平的妻室啊!」他激动的说道。 这话一口,惊讶的非懂湘柔,连薛子平自己也呆住了,不知自个儿哪来的勇气。 毕竟这事尚未告知姑母就光教表妹知道,是太过鲁莽轻浮了,更别说於礼不合。 湘柔瞪大了美眸望住薛子平。「表哥,我不懂您的意思。」 「前些日子我曾修书差人带到京城呈给家父,家书上秉明了我欲向姑母提亲,请姑母将表妹你许配给我。至今已过了月馀,算算这两日该有回音,料想此等亲上加亲的事,父亲大人定是欣然允可的。况且我在信上还提到了表妹知书达礼及种种好处,如此一来,父亲更无反对之理了,是以找才会说表妹你┅┅将会是子平的结发妻┅┅」 「莫非二娘她答应了?」湘柔慌乱了,她对邵风已┅┅如今教她如何还能嫁与他人?她的身与心已是不完整了呵! 薛微有些尴尬。「只因爹爹的回函未至,故而我尚未告知姑母,只要爹爹答应了,姑母当无不赞同之理。」 「不,表哥,湘柔早已决定此生不论婚嫁!」揪住了心,她低喊出口。 「表妹!」料想不到竟会听到拒绝的言语薛子平的惊讶多过困窘。「你┅┅婚姻大事自古以来皆是奉父母之命,表妹你怎可自行主张,更遑论你居然不嫁?这又是为何?」 没有立即回答,湘柔移目望向远处的碧波池,半晌,她恢复了冷静。「方才表哥一开口便要湘柔放弃习琴,湘柔不知──表哥是何用意?」 薛子平一愕,不知湘柔何以突然岔开话题,言及此事。可他性格向来迂直,虽不明所以,仍是有问便答:「那是──记得我上回便说过,表妹之所以习琴是为尽孝道,可是孤男寡女同虚一室,於表妹的名节有损,是以子平才三番两次提醒表姊三思。」 「表哥可听说了任何毁我名节之语?」 「是┅┅曾有听闻。」他向来说下得谎,即便是为了善意。「不过找是绝对不信的!那些谣言只要入我耳里,我必定痛加驳斥,维护表妹的清誉!」 「表哥也听说过了,可想而知,这事已传遍大街小巷了┅┅而且怕是不堪入耳得很。」 薛子平面色一僵,想起柳府下人背地里嚼舌的闲话。「可是那毕竟只是谣传。 表妹玉洁冰清,何须在意那等混帐话!」 湘柔平静的神色叫人瞧不出端倪。「谣言向来可杀人於无形,湘柔自可不在意,只是──表哥若真娶了湘柔,当真也可全然不在意他人的讥嘲讽谤,辈短流长?来日有人识论湘柔贞节时,当真分毫不觉得难堪吗?」 「我──」薛子平蓦然住了口,一口绝不在意便在喉头,硬是逼不出声。 他确实是在意的。 现下他一心羡慕表妹,或可一时置旁人的讥诮於不理。但往後呢?即便是现在,每听得有人说些不堪的闲话,他心底已有莫大的疙瘩。 「你在意的,表哥。」湘柔淡淡一笑,绝艳的容颜中有一抹若有似无的哀愁。 薛子平呐呐无语,无疑是默认了。 轻喟一声,她接受了意料中的答案。「既然在意,若当真娶了湘柔,会快乐吗?」 薛子平身子一震。「婚後你会离开杭州,随子平定居京城祖宅。」声音里充满执拗。 「这会有什麽不同吗?」湘柔轻声道:「即使换了环境,摒弃不中听的话;以往曾经入耳的闲语,表哥仍是记得的。」 「我可以遗忘!只要给我时间!」他固执的辩驳。 「多久?一年?两年?十年?二十年?更有可能穷尽生在遗忘、否中度日,不苦吗?」她眉间锁上轻愁。 「我┅┅」薛子平懊恼的撇开了脸。」子平只知若娶不到表妹,当下便是痛苦!表妹无须多言,子平┅┅不会放弃的!」如何能放弃?他的心早已沦坠了。 湘柔果然不再多说,她定定凝住薛子平别开的脸半晌,淡淡的说:「表哥请回吧,湘柔已无话好说了。」 「我绝对不会放弃的!」他激烈的重申一遍。 湘柔不再作答,轻移莲步出亭而去。 「人家话都已经说得这麽明白了,表哥还是执迷不悟吗?」 清脆的女声蓦然自身後响起,薛子平心惊的回首。立在问心亭外数步之遥的,是柳湘毓。 「毓表妹!?你──你来多久了?」 「你来了有多久,我便来多久。」柳湘毓冷言。实则她是一路暗随薛子平而来的。 薛子平睁大眼,满脸是羞惶之色。「那麽┅┅方才我跟柔表妹说的话──你全听见了?」 「怎麽?瞧表哥念成这样,你们方才说过些什麽话,是旁人听不得的吗?」柳湘毓掩不住讥剌之意。 薛子平面色一变。「表妹说笑了。」 「说笑?」柳湘毓朱唇勾出一朵冷笑。「表哥或者可当我是说笑,可你心上那个人呢?人家的拒绝可不是同你说笑吧?」抑不住的忿懑,出言即尖酸刻保 闻言,薛子平的身体整个僵直了,他侧首,回避柳湘毓直勾勾的利眸。「婚姻大事由父母安排。柔表妹不过一时糊涂,待姑母允可了婚事,柔表妹终究会想明白的!」 柳湘毓冷哼。「好冠冕堂皇的理由!只怕表哥是一厢情愿,到头来白费心机!谁知人有没有把你的一腔真情放在心上。当真落花有意,流水无情。」爱与怨致使她一再口出伤人之语。 「毓表妹你──你为何句句出言讥刺!?」他拧眉。 「我所说的难道不是实话!?」柳湘毓转而激动。「我是在点醒你啊,表哥!你瞧不出来吗?人家压根儿没把你放在心上啊!」为何他对自己因何无状讥刺不能用心明白?她爱他啊! 「这是我的事!你毋须多管。」薛子平背过身,口气执拗。 柳湘毓摇头,不信且气忿。「表哥,你是怎麽了?你不是一向最重礼法、操守的吗?现下不止府里传得蜚言蜚语,不堪入耳,恐怕整个杭州城内也早传遍了咱们家那大小姐的丑事!这样一个名节早破败的女子,表哥你也要吗?」气白了脸,她捧住心,以恶毒的言语诋毁情敌。 「住口!」薛子平蓦然旋过身。柔表妹┅她好歹是你的姊姊,你不该听信外人之言而轻鄙她!」 「无须我轻鄙!她的所作所为早已辱测了她自己!」 「柔表妹是为了姑爹!」他已顾不斯文,出口咆哮。 「说得好听!爹要知道了这事,就算病好了也要活活给气死!你当真以为她孝顺,岂知她骨子里是否yin荡,无耻!」他竟为了别的女人吼她!她恨! 「你-------」 「我错了吗?是表哥你肯面对现实!」心已伤,她要见他也如她一般痛苦。 薛子平抱住头。柳湘毓揭开了他一直不愿去想,不样面对的恐惧。 柔表妹为什麽一味拒绝他?又为什麽暗示了不愿接受父母之命?难道她不知自作主张、违背礼法是大逆不道,人皆鄙夷的丑事吗? 思及这些,薛子平内心经过一番挣扎,末了,他仍然不能舍下已然交出的真情。 「无论众人说些什麽,无凭无据,我终究是不信的。只当它是些平空杜撰的废话!毓表妹若顾念姊妹情分,也当作如是想才厚道。」薛子平一字一句表明立常 「表哥,你连面子也不顾了!?竟要一个早已不清不白的女人」 「不许你再侮辱她!柔表妹不久将是子平的妻子!谁要侮辱了她,便是侮辱了我薛子平!」 柳湘毓惨笑着摇头。「你果然┅┅果然叫那弧狸给迷了心魂┅┅」伤心之馀,仍不忘出击伤人。 薛子平咬着牙,强自忍住到口的怒言,掉头拂袖而报留下柳湘毓一人兀立在原地,叫他的执迷不悔伤透了心。 「怎麽了?有心事?」 是夜邵风一如以往,夜半时分至湘柔闺房为她祛毒,如今四十九日之期将届,湘柔体内的馀毒已很排清。 「没有┅┅」湘柔轻殿的答。 他抚起她低垂的螓首,审视她的眼精。「别说谎。你瞒不过我的。」 湘柔低低敛下眉睫,回开他闪着锐芒的眼。「真的┅┅没有。」 即使已被他看穿了,她仍然不能道出自己的心事。他要的是欢快,而非心烦,更何况是攸关自己的婚事,他┅┅会在乎吗? 不,她说不出口,她怕┅┅怕见到的是令她心碎的回应。 「是吗?」邵风俯首吮吻它的颈子,吻痛了她,刻意在她白的胸前吼出一道道瘀痕,如同烙樱记住,你的身子,你的心智,一切都是我的,永远┅┅不许骗我。」 「嗯。」 他充满占有欲的吮吸弄痛它的身子,但最痛的┅┅还是心。她知道,他不会要她一辈子的。 「你身上的毒已快祛清,届时我会让你真正成为我的女人。」他眼脸微合,大手占有性地揉抚她的身子…… 薄凉的秋意在这几日染上早冬的寒凉,这时节已近呵气成雾。 薛宝宝一派贵夫人的姿态,悠闲地坐在柳家大厅的紫檀木雕花椅上,小口啜着春兰刚奉上的一盎叁茶,呵着叁茶上热腾腾的氤氲白雾,等着家仆请来邵风。 这个把月来爷的病已痊愈了大半,邵风高明的医术自然是救点的关键,功不可没。 可据她了解,名满京师的妙手医,向来要止不定,逗留与否全凭他一己高兴,即使许以万金,亦不见得能多留他一日。总而言之,此人行事狂放率性,当时能请得功做来府里治老爷的痛,连薛玟贾自个儿都觉得意外。 听说邵风那时正在京城里替一位颇有权势的老王爷治病,没想到他竟撤下治了一半的王爷,即刻南下至柳府为老爷治病,至今薛宝宝仍不能理解他为何会如此? 因此,邵风自是薛宝宝奉承有加,得罪不起的大人物,老爷的生死危亡全系於他妙手神术不说,传说中他的身分特殊,连当今圣上亦忌惮他三分,无怪乎那教他随便撤下的王爷大气也不敢喘哼一声。 因此,虽说邵风早已明白提点了不耐烦客套应酬──意即谢绝主人的「打扰」,但她既是做主子的,个把月对客人不闻不问毕竟心有不安,亦不成体统,故而今日才厚着脸皮,让柳府的总管事柳江上明心阁去请来邵风,至少微表她这做主人的关怀之意。 「邵大夫,您这边请,夫人正在厅上等您。」厅门口传来总管事柳江苍老的声音。 薛宝宝闻声赶紧自座上站起,迎至厅门。她可半点不敢怠慢这名贵客。 「邵大夫,请上座。」薛宝宝打起十二分精神来,笑脸迎客。 邵风淡淡一笑,也不多让,对方既请他上座,他便不客气地迳坐上上位。 「柳夫人邀邵某至此有要事?」口气亦是一迳淡然的,相对於薛宝宝的热络,不由得令薛宝宝好生尴尬,分明是拿自个儿的热脸去贴人家冷屁股。 「是啊!」对於邵风明显的冷淡她倒也不在意。「我今日请大夫来是想请教,咱们家老爷的病不知还得多少时日方得痊愈?」这确也是薛贾宝数日来挂心之事。 邵风端起桌上一盅刚奉上的热茶,慢条斯理地吁了几日,方才徐言道:「柳老爷这病已拖了数载,若想一举株拨病根,於柳老爷孱弱的身子恐有贻害,简而言之,欲治此症,切忌躁进。」 「邵大夫所言甚是,只不过──不知咱们家老爷的痛,这会儿好了几分?」说归说,事关自个儿丈夫,她终究心急。 邵风搁下手中茶盅,这才抬眼正视柳府的女主子。「柳老爷的病近来已不需日日灸治,估量已好了五、六成,往後只需定时下针,再日以悉心调养,数月之後此病当可痊愈。」 「邵大夫果真神医!」薛宝宝这才眉开眼笑。「我们家老爷自从犯了这怪病,打南至北也不知请遍了多少大夫,都没能治得半分,幸而有得邵大夫仁心仁术,回春妙手,老爷这病今日方能得救。」少不得又是奉承一番。 「听夫人口音,似非江浙人士。」邵风似不经忘提及。 「邵大夫好耳力,妾身原籍确非江浙,而是冀州石门。」 「冀州石门。」他黑瞳掠过星芒,一纵即逝。「不知夫人与冀州薛氏『鬼蛊门』可有关系?」 刹那间薛宝宝面色一窒,倾刻随即掩去。 邵风已将这瞬微变化瞧入眼底。 「邵大夫真是会说笑。」薛宝宝扬手拍抚心口,一脸的莫名之色。「什麽鬼、又是什麽蛊的┅┅怪吓人的!妾身是来自北地不错,但并不识得邵大夫您提的那鬼什麽门的┅┅」双眼有意无意避开邵风清冷的拌光。 唇角微扯,他淡淡领首。「邵某随口提起,夫人不识得也是自然。」 「是呀!咱们是清白人家,怎会去取那等诡怪名号,就是听也不曾听过哩!」 「是邵风唐突了,夫人莫怪。」他唇角一撇淡笑,暗喻讽意。他有此一问自有用意,「碧凝香」即出自「鬼虫门」。 「我不是这意思,邵大夫您别多心。」薛宝宝眼珠一转,撇清之後,便软兼施,此时又是满脸堆笑了。 邵风略移坐姿,伟岸的身形勾勒出慑人的气魄,狂傲的俊容上多了三分叫人捉摸不定的神采。 「今日即便夫人不邀邵某,邵某也要请夫人移驾厅上,有事相商。」他语锋一转。 「邵大夫有事?说什麽商量,您吩咐便是。」他会有事同自个儿商量?这倒挑起了薛宝宝的好奇心。 「过几日是家叔六十寿辰。邵某有意为家叔设宴热闹一番,想邀夫人同二位小姐,到邵某位於苏州城一处别业做客三日。」 「原来如此,邵大夫开口邀请,咱们荣幸之至,说商量便太客气了,咱们可是求之不得呐!」 薛宝宝确实求之不得,掩不住洋洋得意之色。邵风可非一般豪富官绅,他不仅名气响亮且身分特殊,虽无人确知其来历,却肯定是极不简单的人物。 「只是,」薛宝宝尚有一问。「邵大夫不在府里,那麽老爷的病┅┅」 「夫人尽管放心。柳老爷如今每隔十日下针即可,来回苏州一趟至多不超过五日光景,於柳老爷病情无妨。」 「既是这样那就太好了,这器酒咱们非喝不可了!」她笑得无比欣悦自得。 薛宝宝正得意,厅外忽然传来喧闹声,打断她愉悦的心情。 「柳江,去瞧瞧外头啥事。」使个眼色,她支出柳江瞧个究竟。 柳江领命欲至外头了解情况,岂知前脚未踏出厅门,已迎面奔入一人。来人,是薛子平。 「表少爷,您──」柳江可没瞧见过薛子平这等莽撞模样,一时也呆了眼。 怪不得他,向来薛子平给人的印象是极拘谨的斯文人。 邵风默坐一旁,袖手旁观。 「柳江,退一退去。」薛宝宝柠着眉头发语。这儿可愈来愈不成体统,怎地今日这等无礼,竟挑她招呼贵客时似头蛮牛般闯入。「子平,你倒说说,这麽失礼的闯进来,你可还把我这姑母放在眼底?」话中多有不悦。 薛子平面有赧色,脖子却撑得梗直。「姑母,您别怪我,我明白自己失礼,我之所以闯进来──」他瞧了一旁凝如止水的男子一眼。「实是因为有要事,必须当着您和邵大夫的面说明白。」 「薛公子但说无妨。」邵风不冷不热的音调介入,堂而皇之反客为主。 薛子平不再看向邵风,大有不领情之意。「儿於个把月前曾托人携家书一封呈予父亲大人,内容攸关儿婚姻大事。子平恳求父亲作主,请姑母将表妹──柔表妹许予子平──」薛子平言至此,薛宝宝已然神色大变。「如今儿已收到父亲亲笔回函。父亲回信在此,请姑母过目。」薛子平将薛成兆的亲笔书函呈递给薛宝宝。 薛成兆信上所书,乃是乐成美事,极赞成儿子亲上加亲之举。他自是不知道,薛宝宝对湘柔的憎厌。 亲眼目睹胞兄的信,薛宝宝脸色铁青,地想不到这一向拘谨迂腐的子,今日会出此一招,分明是看准了她难以拒绝。 「姑母,父亲信上已言明了欲与姑母亲上加亲,姑母您┅┅」 「子平!」薛宝宝冷着僵凝的笑脸,犀利的目光似把刀子般直射在薛子平脸上。「你父亲就然同意了,你想姑母能拒绝吗?」 「这麽说──姑母您同意我跟柔表妹的婚事了?」薛子平喜出望外,掩不住的亢然欣喜。 薛打打咬牙领领首,她是不得不同意。一来她极要面子,况且在邵风面前,她可去不起脸。一二者她有秘密握在胞兄薛成兆手上┅┅与其说是看在手足情义上,不如说她同薛成兆是利害相关,岂可为此事翻脸。三者她在那贱丫头身上所种的毒,薛成兆并没有解药,届时他宝贝儿子若有问题必会来求她,正可牵制,到那时可别怪她不顾手足之情了曰「当然。」薛宝宝皮笑肉不笑地道:「不过,这事还得等你姑爹病好些时再说。」 「这个自然。等姑爹身子好些了,我请父亲亲自向姑爹提亲。」他万分诚恳。 「嗯。」薛宝宝冷下眼眉,心下已气得郁窒,神色阴晴不定。 毕竟教一名後生小辈摆布她岂有甘心! 「既然姑母已答应,」薛子平转向邵风,戒备的姿态明显含有敌意。「那麽,有一事务请邵大夫美成。」措辞虽尔雅客气,眼底沛然有挑衅之意。 「请说。」邵风面无表情,星眸淡冷。 「柔表妹向来孝顺,故而同意与邵大夫一室习琴,但如今表妹与子平已有婚约,若再与邵大夫一室习琴恐有悖体之嫌,因此子平希望邵大夫能中止授琴之举。」薛子平勉力不调阅视线,命令自己牢牢对住邵风那两道冷例凛人的寒眸,却教他身上所迸发的森寒沁冷了自己的心头。 邵风的俊颜牵出一撇调入魔味的浅笑。「柳姑娘既与薛公子订下婚约,邵风自然不便再与柳姑娘同室授琴。」语调徐淡得叫人窥不出意欲,波澜不惊的沈定里渗出一抹阴冷味。 薛子平听邵风亲口允诺虽觉如释重负,可心口沈窒的躁恶却未见清缓之势。是邵风那乖冷得几近阴沈的凝定教他不安?抑或是胜利得来太过经易了些,邵风甚至未多置一辞,即刻便同意了。他究竟是何来历?真的只是个单纯的大夫吗?不,不像,那气势┅┅即便是京城里的皇亲贵胃亦及不上万一!即使他浑身透着邪味┅┅「子平,」薛宝宝不悦地打断薛子平的疑思。「你这孩子又怎麽了!邵大夫都应允了,你没半句话说吗?」言下之意是怪责他不知礼,这平日楞头楞脑的儿,今日叫她丢足了面子。 薛子平一怔,回过神来,暗暗皱起眉头。「多谢邵大夫成全。」他心口有着沈甸甸的不安。只见邵风微微颔首,凝在唇角的淡笑莫名擒痛他的眼精,诅咒似地嵌在他心坎儿底,始终挥之不去┅┅
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