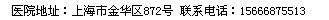您的当前位置:寡趣症 > 饮食调养 > 中篇小说畀愚丽人行连载三
中篇小说畀愚丽人行连载三
畀愚
畀愚:男,年生。年开始小说创作,曾获浙江省青年文学之星称号、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级作家。至今已在《人民文学》、《收获》、《十月》、《当代》、《钟山》、《天涯》、《上海文学》、《中国作家》、《青年文学》等国内期刊发表小说作品二百万余字,部分小说入选《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短篇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21世纪小说年选》、《21世纪文学大系》、《学府年选》等国内各大选刊及各出版社的年度选本,部分小说被改编成影视作品并译介到国外。《钟山》、新浪优秀中篇小说奖、数届浙江省优秀中篇小说奖、第八届“上海文学奖”、第二届“四小名旦”青年文学奖”、首届《上海文学》中篇小说佳作奖、年度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奖、第曾出版长篇小说《碎日》,中篇小说集《站在到处是人的地方》、《罗曼史》等。
丽人行
█畀愚
每年粜米时节久红都会来看望紫云,捎上一些腊肉,带着秋生。这一年,久红走进龚家大门时,怀里抱着还不到三个月的儿子。
紫云的眼睛一下有点红了。她一下子想到了自己。
我们还没有名字呢。久红逗着怀里的孩子说,我们是来求姨娘给取个名字的。
秋生傻笑着插嘴说,我们两个加起来也认不到一升斗的字。
国荃。紫云几乎是脱口而出的。这是家澍在她怀孕时,照着家谱为他们孩子取的名字。紫云说完,从久红手里抱过孩子,亲了会儿,掂了会儿后,吩咐用人去百福楼叫桌菜来。她说,今晚,我们要喝酒。
我们还得回去。久红说,我们搭船来的。
住两天,到时我叫船送你们回去。紫云说着,抱着孩子转身就往后堂去。
夫妻俩对视一眼,看到的都是对方眼里的诧异。
傍晚,紫云在酒桌上拉住久红的手,说,把孩子过继给我。
不行。久红说,国荃是我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他姓杜。
紫云看了眼秋生,忙说,那让我认他做干儿子。
姐。久红笑了,说,你是他姨娘。
紫云一愣,眼神瞬间变得暗淡。她收回手,抓起酒杯,默默地喝下一大口。
久红这时笑着又说,姐,你该找个人嫁了,守着这么大一个家是孵不出孩子来的。
紫云没想到久红都敢当面数落自己了。她脸随心转,这顿三个人的宴席一下变得沉闷与无趣。
夜深后,紫云在床上辗转反侧,脑子里出现的人一会儿是家澍,一会儿又是刘昭铭。到了最后,她的鼻息间只剩下刘昭铭身上那股烟草的气息。
有一次,刘昭铭曾亲口对她说,我之所以一直留在秀州城里,为的就是你。他说,照现在的局势看,只怕会越来越乱,你需要有个人来保护。说着,他拉起紫云的手,看着她的眼睛说,我有这个责任,也有这个能力。
紫云知道这一天迟早会来,但她还是摇了摇头,轻轻地抽出手掌,说,我不要人保护,我安安心心地守我的寡就够了。
那让我陪着你,我们一起缅怀他。刘昭铭说着,重新拉过紫云的手掌,把它紧紧地攥在手心里,说,我不能让你像花一样枯萎掉。说完,他低下头,又说,我这辈子唯一遗憾的是没能早一天见到你……只要早一天就够了。
紫云的鼻子莫名地一酸,竟然在他面前差点就掉下眼泪。
刘昭铭是个细心又专情的男人。他跟家澍不同,他做每一件事首先想到的是紫云。为了避免用人们的闲言碎语,他从来不会在龚家留宿,通常都是约在外面,先一起吃顿饭或是听场戏,然后在他租住的房间里睡到半夜时起床,亲自把她送到龚家的后院门外。紫云就是在那里第一次尝到了吻别的味道。
这种偷情一样的时光,让她觉得别样的刺激,同时又充满了柔情与蜜意。
有时候,他们还会赶去省城幽会,趁着刘昭铭出差的机会。两个人分乘两班客轮,先后到达约定的旅馆,在那里就像夫妻那样无拘无束地吃饭、洗澡、做爱。除了这三样,紫云在事后几乎想不出他们还干过什么。
但是,紫云还是说出了她藏在心里一直想问的那句话。在一次事后,她枕在刘昭铭的胸口,说,你从来没回过家……你不想你的太太,不想你的孩子吗?
我哪来的太太?刘昭铭笑了,但他很快收敛起笑容,说,我的家早就没了。
那你干吗不成一个家?你快四十了。紫云抬眼看着他的下巴,用力把最想说的那半句话咽回肚子里。
我何尝不想?娶你做我的太太,跟你生一群我们的孩子。刘昭铭说,可我不能那么做。
紫云没问为什么。这么多年来的经验告诉她,男人是不能靠逼问的,男人只能靠引诱。她把头一点一点地埋下去,刘昭铭却把她拉上来,用力地搂进怀里。
这天晚上,刘昭铭的表情从来没有那么凝重过。他在紫云的耳边说了很多事,从当年日本人占领南京杀光他全家开始,一直到那天晚上,在龚家第一次见到紫云。他说,人就是这么奇怪,我始终都觉得你应该是我的妻子,我才是那个该娶你的人。
那你为什么不娶呢?紫云最终说出了那句她最想说的话。
刘昭铭没有回答。他整夜都以一种温柔的姿势搂抱着紫云,就像生怕她会消失。
从长江前线溃败下来的国军士兵拥进秀州城当天就洗劫了隆升米行。同时遭到洗劫的还有整条街的商铺。
刘昭铭带着卫兵匆匆赶到时,紫云正脸色发青地站在库房门口。她从鼻孔里哼出一声冷笑,说,以前还知道打个收条,现在就干脆用枪顶着你的脑袋明抢了。
这些都是身外之物。刘昭铭示意卫兵退下后,说,今晚有船,我们离开这里。
紫云吃惊地看着他,说,为什么?
南京失守了,这里很快就会沦为战场。刘昭铭说,我们先到上海,再去广州。
我不走。紫云断然说,出了这座城,我什么都没有了。
刘昭铭目光忧郁地看着她,说,留在这里,你照样会什么都没有。
紫云始终犹豫不决,一直要到快吃晚饭时才横下一条心,让人把吴掌柜请来,亲手为他斟上一杯酒后,指着桌上的一串钥匙,说,这个家你替我看着,要走的人,你支他们三个月的工钱,不走的,你帮我照料着。
吴掌柜低头沉默了很久,说他在龚家已经都快四十年了,辛亥年剪辫子的那阵,都以为天塌下来了,可是天没塌,还是好好的。日本人打进来时,他又以为天要塌了,可结果还是把小日本赶走了。吴掌柜用酒润了润嘴唇,抬眼看着紫云,说,少奶奶,你别慌,天塌不下来的。
谁说天要塌下来了?紫云莞尔一笑,举起酒杯,说,吴叔,我就是出去几天,活了这么大,最远的地方我只去过省城。吴掌柜放下酒杯,说,少奶奶你放心,你走的时候龚家这个样,等你回来,还是这个样。
紫云点了点头,又敬了吴掌柜一杯后,开始吃饭。
饭后,她独自来到家澍的牌位前点了一炷香,站在那里,出神地一直看到它燃尽,才回屋收拾细软。
刘昭铭早已等候在人头涌动的码头。在两名军警的护卫下,他们登上轮船,刘昭铭却站住了,把一张纸条塞进紫云手里后,抓住她的手,说,你在上海等我,我会来找你的。
紫云睁大眼睛,说,不是说好一起走的吗?
我还有点事,我会来找你的。刘昭铭说着,松开手,扭头就走,但马上又回过身来,一把将她拉进怀里。轮船上到处是人与人的声音,他无所顾忌地把舌头伸进紫云嘴里。
船开出很久后,紫云才回过神来,茫然四顾,只见船上好多眼睛仍在昏暗的船灯下盯着自己。
刘昭铭留下的纸条上写着一个地址。紫云在那家旅社入住不久,进攻上海的战役就打响了。整整半个多月,她日夜都在房间里等待心爱的男人,直到一天早上醒来,发现枪炮声静止了,大街上密密麻麻睡满了身穿黄布军服的解放军士兵。
紫云站在窗口忽然笑了。她这辈子都从未这样放肆地笑过。一直笑到泪流满面,她才滑坐到地板上,双手抱紧自己的两个膝盖,埋着头开始哭泣。
为了欢庆远在北京的开国大典,秀州城里锣鼓喧天、红旗飘扬。
紫云在这天由上海回来,穿了一条士林布的旗袍,裹着一块格子布的头巾,就像个过客一样,匆匆穿过人流如潮的街市。但她去的地方不是龚家,也不是隆升米行。紫云径直走进了乌衣庵的大门。
年迈的师太在心底发出一声叹息后,领着她去了曾经住过的房间。
紫云站在门内,说,这一回,我不走了。
师太一笑,双手合十,说,该来的时候来,该走的时候走,少奶奶不必太介怀,
一天,吴掌柜领着一名年轻的解放军士兵走进乌衣庵时,紫云正在清扫院子里的满地落叶。吴掌柜小心翼翼地说,军管会的同志想请少奶奶去一趟。
紫云直愣愣地看着吴掌柜,好一会儿才对着那名年轻的士兵,说,要我去干吗?
士兵显然已经有点不耐烦了,说,快走吧。
紫云连身上的素衣都没有换掉,就被那名士兵带进了军管会的大楼。这里也曾是刘昭铭办公的地方。紫云的心一下就跳到了嗓子眼里。
军管会的齐同志是个面目沧桑的中年人。他为紫云倒了杯白开水后,在她对面坐下,自我介绍说,他以前是新四军浙北游击队的特派员,在这座城里还做过几天小生意,当然那是为了开展地下工作。齐楚南话题一转就说起了家澍,一直说到紫云睁大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他那张沧桑的脸。
原来,刘昭铭说得没错,家澍生前一直用家里的财产暗中资助新四军。
正是这些经费帮助我们渡过了好几次难关。齐楚南说,我们是不会忘记老朋友的。
那他是你们的人?紫云终于开口说话。
是朋友,肝胆相照的老朋友。齐楚南说完,换了种语调,从国际形势一直说到国内形势。这些紫云都不懂,却听得特别认真。最后,齐楚南站起身,一挥手,说,他们在战场打不过我们,就想用经济来封锁我们,他们是要把新中国这个初生的婴儿扼杀在摇篮里,但这是做梦,是妄想。
紫云这才明白,冬天来了,秀州城里跟往年一样开始缺粮了。她不假思索地站起来,说,我听政府的。
齐楚南赞许地点了点头,说他知道龚家已经不比当年了。他说,你可以回去考虑,隆升米行怎么说也是百年的老字号了,我是希望你能出来带个头。
紫云还是说,我听政府的。
齐楚南又赞许地点了点头,说,少奶奶真是巾帼不让须眉。
舍不得的人是吴掌柜。他几乎是含着眼泪说,还是折成公债吧?都捐出去了,开年我们拿什么来收粮?
紫云没有说话,步履缓慢地穿过行人稀少的街道,走到乌衣庵的大门口。
吴掌柜在台阶下站住,叫了声,少奶奶。
紫云这才回头看着他,说,这些都是身外之物。
几天后,齐楚南带队敲锣打鼓地来到乌衣庵,亲手把一朵大红花挂在紫云胸前,说,我代表人民政府感谢少奶奶的义举。
紫云半天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一瞬间,她有种热泪盈眶的感觉。晚上,紫云捧着那朵大红花盘坐在师太的禅房里,低着脑袋,说,我把龚家的根基换了这么一朵大红花……到了那一天,我该怎么去跟他们交代?
少奶奶这是大彻大悟。师太捻动着手里的念珠,说,黄泉路上,能攥进手心的只有自己那十个指甲盖。
久红第二胎生的仍然是个男孩。她抱着孩子来到龚家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龚家的前厅已经拆完,许多男人正用外面挑来的泥土填平中庭的荷花池。久红站着看了半天,心想,原来城里也开始闹土改了。
而更让她感到惊讶的是紫云。她不仅剪了一头齐耳短发,连平日里的旗袍也换掉了,身上穿的是件深蓝的列宁装。
久红睁大眼睛看了好久,才没头没脑地说了句,你就像个工作组里的女干部。
紫云连说话的语气都变了。她微笑着说,新社会就得有新气象。姐妹俩在后院的屋里坐下后,紫云告诉她用不了多久,外面就会变成一家幼稚园了。新社会讲究的是男女平等,女人不能光待在家里喂孩子,还得出来工作,这叫自食其力。那她们的孩子怎么办?白天就放到这里来。紫云说,这是秀州城里第一家幼稚园。
那我这回就来对了。久红一边撩起衣襟喂奶,一边说,我跟秋生商量过了,我们把国新过继给你。
紫云愣了半天,一直到久红喂完奶。她一把抱住孩子,把脸埋了下去,使劲地嗅着国新的小脸蛋,好一会儿才抬头,惊喜地说,你看,他尿了,他尿了我一手。
久红在龚家住了两天后,留下儿子回了钱王甸村。临走时,她仔细地端详着紫云的脸,说,姐,你还是把头发留起来好看。
一下子,紫云觉得有点难受。为了掩饰,她低头不停地嗅着熟睡的国新的小脸。
断奶期的孩子最难带的时候是在夜里。他既不吃也不睡,就知道闭着眼睛拼命地哭,两只小脚拼命地蹬被子。紫云实在是没办法,只好撩起衣服把奶头塞进他嘴里。孩子倒是不哭了,可一个夜里下来,她的两个奶头已经被啃得鲜血淋漓,疼到钻心。
一天晚上,紫云从熟睡的孩子嘴里拔出奶头,忽然流泪了。她含着泪,看着孩子,说,傻儿子,你喝的可是妈的血。
幼稚园快落成的时候,秀州城里到处传唱着雄赳赳,气昂昂, 。紫云当场决定把它取名为抗美幼稚园。不仅如此,一年后,在给孩子报户口时,她还把国新更名为援朝。
就叫龚援朝。紫云对派出所里的公安同志说。
现在,紫云不光是抗美幼稚院的院长,她还是秀州妇女界的代表。白天在园里带孩子,晚上还要在灯下为前线的 纳鞋底。紫云每天都觉得很累,闭上眼睛就能睡着,但同时也觉得从来没有这么踏实过,踏实到可以不去想那些铭刻在心头的往事。
可是有一天,齐楚南忽然来到幼稚园。他把紫云叫到操场,说,上海那边抓获了一批美蒋特务,其中有个叫刘昭铭的,让他漏网了。
紫云的眼睛一下直了,人却很快就变得恍惚。她慢慢地伸手,捏住衣服的下摆,扭头看着围墙边的那两株梧桐树。阳光正穿过枝叶间的缝隙,照得她睁不开眼睛。
抗战时,他是龚家澍的上线,我想你应该见过这个人,他是军统在秀州地区的负责人。齐楚南继续说,他极有可能潜逃到了这里。
我记得他。紫云用了很大的力气,才喃喃地说,原来他还活着。
他逃不出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齐楚南把张开的手掌有力地一握后,接着告诉紫云,为了配合上海方面的搜捕,他去省城查阅了大量日军遗留下的档案,发现刘昭铭不仅是国民党的特务,他还是个汉奸,是个可耻的叛徒。
原来,抗战胜利的前夕,刘昭铭在去杭州执行任务时被日军的特高课诱捕。他变节了,出卖了许多与他患难与共的战友。家澍与宝钗就是其中的两个。
紫云听完这些,再也站不下去。她走到旁边的一个秋千架下,抓着那根绳索动作迟缓地坐了上去后,张了张嘴,却没能发出声来。
我也失去过亲人,我了解你的感受。齐楚南站到她面前,说,我们是经过慎重考虑,才决定告诉你的,你有权知道,这是历史的真相。
三十七岁那年,紫云第二次嫁人。她的婚礼简朴而热烈,就像每年元旦都会举行的联谊会。宾客们聚集在抗美幼稚园的礼堂里,长条桌是小朋友的课桌拼接起来的,大家猫着腰并排坐在小板凳上,喝着红茶水,嗑着葵花子。人武部长致完证婚词,大家鼓一次掌;街道主任介绍完当前的形势,又鼓一次掌。
直到所有的掌声都平息下去,大家按照习俗开始闹新人时,久红起身去了外面,一屁股坐到台阶上。她曾经无数次地想象过与王锦清的重逢,却从来没有想到过,跟他结婚的女人竟然会是紫云。
一九五五年的国庆,空气中到处弥漫着金桂腻人的花香,而让人更加兴奋的是秀州城里终于通上了铁路。第一列火车到站停靠时,率先下车的是从朝鲜归国的 战士。他的黄军装上挂满了功勋章与纪念章,一下车就忙着立正与行军礼,与前来接车的首长一一握手,接着又行军礼。
紫云挤在妇女代表的队伍里见到锦清时,一眼没认出来。她只是觉得这个 同志有点面熟。第二次,在英雄事迹报告会上,紫云坐在台下遥望着他那张不再白皙的面孔,不禁再次感叹命运的神奇,它让钱王甸村里最有名的败家子与花花公子都能成为战斗英雄。
他们的第三次见面是在两个月后,锦清来幼稚园为小朋友们做报告。他就像从来不认识紫云一样,一见面就抬手行了个军礼,叫了声,园长同志。
紫云略带失望地说,王锦清同志,你不认识我了?
锦清这才笑了,握住紫云的手,说,怎么会呢?我前几天还梦见你呢。
狗是改不了吃屎的。紫云在心里说,现在,他更有本钱去祸害那些女人了。
报告结束后,紫云把他送到幼稚园的门口。两人握别时,锦清没有马上松开手,而是有点莫名其妙地说,组织上已经批准我转业了。
紫云礼节性地说,欢迎你加入到地方建设中来。
几天后,锦清去了紫云所在的街道,找到妇女主任的办公室。不等他把话说完,妇女主任就笑着打断他,说,你们这些枪林弹雨中过来的同志就是性子急……好吧,你说,你看上哪家的闺女了?
锦清说,抗美幼稚园的钱紫云。
妇女主任愣了愣,说,你了解她吗?
了解。锦清说,我们本来就是一个村的。
人家可是结过婚的,还拖着个油瓶。
我知道。锦清说,她男人死了十年了。
看来你是摸过底了。妇女主任笑着说,可你不知道,她男人活着的时候是个国民党。
我知道,他死在了日本人手里。锦清说,毛主席、周总理都给张自忠题过字呢。
谁是张自忠?妇女主任拧起眉毛,说,你们一个连队的?
锦清说,抗日英雄,国民党的将军。
妇女主任又愣了愣,不敢答应,也不敢不答应。送走锦清后,她摘下袖套,就急匆匆地赶往人民武装部。
人武部长是个参加过淮海战役的老同志。他不以为然地说,给国民党当过老婆又怎么样?把她娶过来,不就是我们的胜利果实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妇女主任说,王锦清同志是 的功臣,只要他一句话,哪个黄花大闺女不愿意嫁给战斗英雄?
那也要先让人家对上眼。人武部长站起来,由衷地说,从战场活着回来的人不容易,不就是娶个老婆吗?你要相信我们的 同志,他们把美国纸老虎都能赶过 去,还改造不了一个国民党遗留下的婆娘?
问题最后卡在了紫云那里,但那已经不是问题。妇女主任亲自上门,苦口婆心地谈过两次后,把紫云叫到她的办公室,语气凝重地说,这是对你的一次考验,放着最可爱的人不嫁,你还打算嫁给谁?
紫云说,我谁也不嫁,我就守着我的援朝过一辈子。
为了儿子,你更应该嫁。妇女主任说,哪个孩子不想有个当英雄的爸?
婚礼仪式过后,紫云还是决定在屋里摆了一桌。菜都是她跟久红一起烧的。在厨房里,她像是在安慰自己似的说,这样也好,至少对援朝没有坏处。
久红充耳不闻,只顾闷头在墩板上剁菜。自从见到锦清,就像一阵风吹过了钱王甸村的芦苇荡,她的脑子里一直在唰唰作响,飘满了漫天的飞絮。
姐妹两家围着桌子吃饭时,久红拿过秋生的酒杯,先是突兀地叫了姐夫,然后把酒杯举到锦清面前,说,姐,我敬你们两个一杯。
紫云蓦然地想起了许多事。她按住锦清的手,对着久红说,都是自家人,不用敬不敬的。
第二天,久红在回钱王甸村的船里,冷不丁地对秋生说,以后,我们再不去他们家了。
秋生摇着橹,说,你不想援朝了?
是国新。久红声色俱厉地说,你儿子叫杜国新,他不叫龚援朝。
婚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紫云都觉得自己又有点中邪了。特别是在床上的时候,眼前常常会浮现出家澍的面孔,一会儿又变成了刘昭铭。这是种奇怪的感受,好像趴在她身上的人不是锦清,而是他们三个,在黑暗中轮换交替着。一天夜里,她在做着的时候忽然流泪了,莫名其妙,却又不可收拾。
锦清支着半个身子在被子外面停了一会儿,说,你这是怎么了?
紫云在黑暗中摇了摇头,双手扳住他的肩膀,把他使劲拉进怀里后,开始变得主动,甚至还有那么一点的疯狂。
锦清却十分冷静。他在事后宽慰地说,这没什么,谁的心里面没藏着点事呢?
紫云还是没有说话,温顺地蜷缩进他怀里,第一次一丝不挂地在他的被窝里睡到天亮。
锦清的身上布满了伤疤,特别是胸口的枪伤,子弹击断了他的一根肋骨,弹头至今还留在肺里。一到冬天,他都会像得了哮喘一样,呼吸中带着啸声,吐出来的痰里面沁着血丝,而这个季节也是他性欲最亢奋的时节,几乎每天晚上都会把紫云从儿子的被窝里拉过来。
但与性相比,锦清其实更喜欢的是喝酒。一到傍晚,街坊邻居们都会自动聚集到他家里,端着各自的饭碗,或坐或站地围在那张八仙桌前,陪着他喝酒,听他讲朝鲜战场上的故事。锦清是个特别能说的人,从 到上甘岭,从联合国军的黑人团到美国空军扔下来的燃烧弹,好像发生在朝鲜的每场战斗他都参加过。有时候,他还会从中山装的口袋里掏出一份《人民日报》,一边喝着酒,一边给大家讲时事,一起学政治。
锦清转业后在粮管所里当保卫科长兼民兵连长,每年都被评为学习时事与政治的积极分子。
可是,紫云受不了每天晚上这么多人挤在家里面,吵吵嚷嚷的,走马灯似的进进出出,但又不好直说,她只能婉转地提醒锦清少喝点酒,想想到了冬天喘不上来的时候。锦清却毫不在意,说酒就是他的命,要不是这一口,他这条命早就留在了朝鲜的冰天雪地里。
那就关起门来,一个人喝。紫云最终还是说出了心里话。她一边收拾桌子,一边说,你又不是说书先生,你不能把家里当成茶馆。
锦清愣了愣,抬眼看着她,说,这里也不是龚家大院了,你也不是龚家的少奶奶了。
一下子,紫云就像被人甩了个耳光,脸涨得通红,半天都没说出一句话来。
夜深后,锦清把手伸进紫云的被窝里,拉了拉她,没见动静,就叹了口气,说,被家里人说,总比让外头的人说要好,外面让人说多了,说不定哪天就有一顶帽子掉到你头上。
紫云说,你听到什么了?
现在没人说,不等于日后也没人说。你跟他们不一样,你不是从群众中过来的,就更应该主动到群众中去,要从骨子里跟群众打成一片。
锦清仰面靠在枕头上,就像坐在粮管所的办公室给人做工作,一直说到紫云主动钻进他的被窝,才一拍她的屁股,说,这就对了。
紫云却始终活跃不起来。她幽幽地说,你一开始就不该娶我这样的人。
锦清兴致勃勃地说,我是毛主席派来改造你的。
援朝上小学那年,抗美幼稚园被正式命名为秀州中心幼儿园。次年,礼堂沿街的那面墙被打掉,办起了公共大食堂,一到饭点就挤满了人,但更热火朝天的是操场上。那里并排砌着三口炼钢的小锅炉,通红的炉火日夜不熄,嘹亮的广播声更是彻夜不绝。
紫云白天在教室里教孩子们唱儿歌,没课的时候就去大食堂帮忙,担水、择菜、洗洗涮涮,哪里需要帮手,哪里就能看到她的身影。到了晚上,安顿好儿子,她仍旧回到大食堂,擀完面条、蒸熟包子,就守在那里,等着放完卫星的师傅们吃宵夜。她曾由衷地对锦清说,累是累的,可我心里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踏实过。
可是有一天早上,站在幼儿园门口迎接小朋友时,她忽然看到一个人,站在街对面的电线杆旁,穿着灰布的中装棉袄,裹着围巾,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紫云一眼就认出了镜片后面的那双眼睛。
这些年,刘昭铭一直都潜伏在秀州城外的一所乡村小学,但他每年都会进城,有时在幼儿园门外,有时在紫云洗衣服的河对岸或是买菜途中,远远地看她一眼,然后默默地回到乡下。然而,这些刘昭铭都没有说。他坐在紫云家里的那张八仙桌前,仔细地擦完眼镜片,抬起眼,一眨不眨地看着心爱的女人,说,你瘦了。
紫云出不了声。她只觉得呼吸停止了,就连心跳都快要没有了。
刘昭铭兀自一笑,低下头,又说,有一年,我看到你在河边洗一件男人的衣服,我以为,我又一次失去了你。
紫云终于开口了。她看着敞开的屋门,无力地说,你再不走,我要喊人了。
你要喊人,就不会让我进这扇门了。刘昭铭戴上眼镜,慢慢地伸出手,把紫云紧攥着的一个拳头握进手心,说,如果我因你而死,那对我是一种解脱。
你把他出卖给日本人的时候,想过他会解脱吗?紫云喃喃地说完,回过头来,泪水却不争气地蓄满了眼眶。
你说家澍吗?他们的话你也相信?刘昭铭忧郁的眼神变得更加忧郁。他长久地注视着紫云,一直看到她低下头,才开始述说起当年,他忽然被命令潜伏善后。整整十年,他躲在乡下,像只藏在地洞里的老鼠,为的就是今天。刘昭铭说,现在我自由了,我只求你给我一个弥补的机会。
紫云听到的却是自己在上海那家旅社里凄厉的哭声。她摇了摇头后,从刘昭铭的手里抽出那个始终紧捏着的拳头,撑着桌子站起身,慢慢走到门边,回过头来。
阳光从门外斜射进来。紫云的脸上一片幽暗。
我已经安排好了,我们去香港。刘昭铭走到紫云面前,把一张纸条塞到她手里后,又说,三天后,我会等在那里,你可以不来,也可以带着公安过来,但我会等在那里。
纸条上的地址是省城的那家旅馆。紫云永远不会忘记她跟刘昭铭留在那里的短暂时光。然而三天后,当省城的公安包围了整座旅馆,却并没能抓获这名潜伏了十年的特务。刘昭铭一直坐在旅馆斜对面的一家牙医诊所里,隔着玻璃望着外面的大街。他的嘴里咬着一块浸血的棉花。
春天来临后的某天傍晚,一辆军绿色的吉普车拉着紫云驶到一座办公楼的后门,一名面容严肃的秘书引着她走进一间会客室。早已升任为地委常委的齐楚南满面春风地从沙发上站起来,老远就伸出手掌,说,钱紫云同志,这次请你来,是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刘昭铭在偷渡澳门的船上被捕距今已经三个月。这三个月里,他日夜接受审讯,写成的交代材料足足有一尺多高。可是,当问到为什么要冒险带着紫云潜逃时,他低下头,沉默了很久,才从第一次在龚家的灵堂里见到紫云说起,他把什么都说了,就是只字不提他们如火如荼相爱的那段日子。说完,刘昭铭抬起眼睛,望着审问他的那两名公安,发出一声苦笑,说,我相信三民主义,我也相信一见钟情,可到头来,这两样都耍了我。
我们今天来,主要是感谢你,正是你提供的线索,让我们最终捕获了大特务刘昭铭。坐在齐楚南旁边的一名中年公安说,现在,请你如实地告诉我们,你跟刘昭铭到底是什么关系?他为什么甘冒被捕的风险非要带你走?
紫云的脸白得就像一张纸。这个时候,她特别地想哭,想流泪。可是,她强忍着,一直忍到整个人都在椅子里瑟瑟发抖。
你不用怕,这不是审问。中年公安换了种语气,说,我们知道,你是爱国的工商界人士,为新中国的建设做出过一定的贡献,我们只是要向你查证一些情况。
他是害死我前夫的凶手。紫云终于开口说,他是罪有应得。
这些我们都知道。中年公安说,但这构不成他要带你潜逃的理由。
那你们问他去。紫云抬起眼睛,说,我也想知道为什么。
离开会客室时,齐楚南亲自把紫云送到门口,再次握着她的手,说,紫云同志,别往心里去,这是我们必要的工作程序。
紫云点了点头,坚持要步行回家。她穿过幼儿园的操场时,炼钢炉里刚刚放出一颗卫星。在一片欢呼声中,锦清从人堆里挤出来,一见到她就笑呵呵地掸着衣服上的灰尘,说,今晚这颗卫星放大了。说着,他凑近紫云,笑着又说,看你这副丢了魂的样子。
秋生死在开挖红旗塘的工地上。他被轰然坍塌的堤坝埋葬。跟他一起被埋的还有附近各村的几十名男女劳力。公社书记当晚就赶到现场,手电照着漆黑如山的工地,他不禁勃然大怒,你们忍心让牺牲的社员同志埋在下面过夜?
想挖也没这个力气。工地的总指挥是公社的副书记。他无可奈何地说,再这样饿下去,这颗卫星只怕是放不起来了。
公社书记没说话,摸黑登上一个土坡,双手撑着腰,就像个决战千里的将军在望着脚下黑压压的战场。
工地总指挥紧随其后,小心翼翼地说,要不,报上去吧。
怎么报?公社书记猛然回头,说,这么一点小事,让毛主席知道了,这不是给他老人家添堵吗?工地总指挥吓得一缩脖子,说,他老人家会知道这里?
公社书记没有回答,重新望着无边的夜色,说,一定要把遇难的社员们挖出来,还要抚恤好家属。说完,他想了想,以商量的口气,又说,你去县里争取一下,每户发五斤粮票吧。
工地总指挥说,城里人才用那玩意。
那你叫我怎么办?公社书记双手一摊,说,这不是困难时期嘛。这不是巧媳妇难做无米之炊嘛。
紫云全家提着半袋米赶到钱王甸村时,秋生已经下葬。
久红神情木然地坐在一张板凳上,用一种陌生的眼神盯着他们夫妻俩看了很久,才喃喃地说,第一次进城时,他就想拍张照片的,可我没舍得……他连一张照片都没留下。
说着,她一下子号啕大哭起来,声音尖得吓人,双眼通红,却流不出一滴泪水。
紫云把援朝拉到她面前,说,我们一听说就赶来了,本想让孩子见上一面的。
挖出来的时候都烂了。久红一下止住哭声,仰起脸,说,我都没把他认出来。
紫云怔怔地看着她那张因浮肿而显得水亮的脸,再也找不出一句可说的话。
锦清坚持要去村里转一转。这是他离开钱王甸村后第一次回到家乡。走到以前王家的那块地基前,他感慨地对紫云说,还是战争年代好呀,生的光荣,死的伟大。
第二天一早,趁着紫云拉援朝在院子里洗漱时,久红站到锦清面前,忽然说,要是你当年没溜走,我的日子不会这样的。
锦清一惊,忙看了眼正从井里往上打水的紫云,说,当年我要是没溜走,现在烂掉那个就是我了。
久红的眼睛一下红了,慌忙伸手撑住墙,张着嘴巴一直到紫云抱着脸盆进来才合上。
粮管所的消防船来接他们一家三口时,紫云见久红一手挎着个包袱,一手拉着国荃,走路都有点摇晃了,却非要把他们送到村边的渡口。紫云在心里动了一下,看了眼锦清。
久红到了渡口,把包袱往儿子手里一塞后,跪在紫云脚下,使劲把儿子推到紫云面前,说,姐,你让他们兄弟俩在一起吧。
紫云忙去拉她,说,你这是干什么?
国荃也在这时叫了声,妈。
久红犟着不起来,又说,姐,你就当养条狗吧。
紫云扭头看了眼锦清,见他两只眼睛直愣愣的,就蹲下身,拉着久红,说,那你就什么都没有了。
久红跪在地上说,没了总比都饿死要好。
未完待续
白癜风药膏白癜风能治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