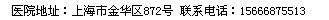您的当前位置:寡趣症 > 临床体现 > 扎西才让文学作品散文我的杨庄节选
扎西才让文学作品散文我的杨庄节选
我的杨庄(节选)扎西才让西藏画家德珍作品《我的父母》父亲的时代
如果说杨庄要出人物,那么我的父亲,算是个人物:他是庄村里的第一个干部。
他是县教育局的小职员,常年住着公家破旧的房子。白天,他热情工作。夜里,烧暖了他的铁皮炉。炉子上的铜壶,在暗室里喷着百姓生活中的热气。他睡在单人床上,身边总是放着一本黄皮书。那书在他的呼吸声里,渐渐浸淫了人间的气息。那不是赵树理的乡村小说,也不是郭沫若的旧诗集。那书上,只讲与民族教育有关的国家大事。
听说在他生活的县城里,街道上车水马龙,商店里琳琅满目。高高的柜台后,一脸豪气的售货员噼噼啪啪打着算盘,她的身后,布料、盐巴、火柴等货物堆成了小山。医院里,大夫和护士穿着白大褂,像极了传说中的仙人。粮站里,储藏着一袋又一袋可以做出雪白的馒头的麦子。甚至那南山上的树木,也是高大浓密的,密林深处百鸟啾啾,公然繁殖。洮河里有白鱼出没,水面上时时腾起如云似雾的云翳。我们一直膜拜的东山上的那座寺院,听父亲说是庄严肃穆的,在阳光下闪耀着金光。夜幕降临后,会有佛灯突破黑暗,显出神界的祥和又神秘的瑞气。
那时,父亲习惯了长途跋涉。他喜欢走四十里的山路,回到杨庄,这个人们说有神灵栖居的村子。途中,夜空里星辉高悬,晚风鼓荡着经幡。他的往事随风而来,缠绕不息。在北方深邃的天幕下,他想起自己的今世,禁不住流下两行热泪。山下静静流淌的洮河水,波闪着他猜想的后世。
在他的一生中,除了孝父敬母、生儿育女、爱乡亲邻,他没做出其他伟大的事。然而有人说,作为一个读书人,能吃上公家饭,这就够了!
西藏画家德珍作品《我的祖父母》某个舅爷“作为一个读书人,能吃上公家饭,这就够了!”
这样评价父亲的,是我的一个远方来的舅爷。
对生活在乡村的我们来说,舅爷,就是一个温暖的字眼。但那个舅爷,却给我们兄妹们带来了恐惧和惊慌。
那一次,他骑匹高大的枣红色的马来了。我爷爷和他盘腿坐在炕上,喝酒。他大声划拳,大口喝酒,大声地责骂我爷爷。
我父亲从县城返回,刚一踏进房子,就被这个舅爷灌了三杯酒,弄得父亲面红耳赤的,像做了亏心事。
这个舅爷长得比父亲还年轻,在我爷爷上厕所的间隙,他评价父亲说:“你能孝敬父母,是好事!能生下这么多娃娃,也是好事!能在村子里有身份有地位,更是好事!作为一个读书人,能吃上公家饭,这就够了!但你见了我,一口一个舅舅,就不是好事!”
他拉住父亲,要称兄道弟。父亲只好举杯道歉,一个劲地自饮,仿佛辈分是个很可怕的东西,不能侵犯,也不能被侵犯。侵犯了,或者被侵犯了,就只能自己惩罚自己。
我们兄妹们躲在窗户外,静听着房内的一举一动。我忍不住好奇心,往屋里偷看。这个举动,被这个舅爷发现了,像变戏法那样,他从腰里抽出一把刀子,有力地插到炕桌上。
父亲吃了一惊,上完厕所回来的爷爷也吃了一惊。伏在窗外的我们一哄而散,在惊慌中躲进房后的山林。
这个舅爷上到房顶,用目光搜索着我们,用语言搜索着我们。我们屏住呼吸,藏在树后。相隔了二三百米,我的四岁的妹妹还是由于惊慌而大哭起来。
这哭声,击退了这个舅爷,他终于踩着梯子,一层一层下去了,再也没有出现。
多年之后,爷爷早就离开了人世。我们只好问父亲:这个舅爷是谁?父亲想不起来,他说,在七十年代,你们的舅爷有好多个,我不知道你们问的是谁。
我们只好把这个舅爷在记忆里封锁起来,以便我们当着孩子的面喝酒之时,不让他轻易地跑出来,把我们的孩子驱进山林,不让他给我们的孩子留下一段抹不去的阴影。
西藏画家德珍作品《姐妹》妹妹说起妹妹,一些记忆总是无法抹去的。梳理与杨庄与妹妹有关的记忆,总觉得我和妹妹,是在相依相守的过程中长大的。
比如说有一个阴天,母亲和姐姐们去乡上磨面,只留下我和妹妹两人守在家里。
她们离开后,老天爷开始下起雨来。我们感觉那雨水和前年一样多,和去年一样多。从房檐上一点一滴地滴下来,滴下来,在我们的心里,慢慢地积蓄起来,形成了看不见却能感受得到的湖泊。
炉盘上,那盛满水的黄铜茶壶,把火的能量都吸收了。仿佛过了好多年,水突然开始沸腾,发出吱吱吱的声音,像一个贫穷人家的婴孩,被噩梦惊醒过来,尖声惊叫。
我们都走到院子里,侧耳静听亲人有没有回来。
后来,雨停了,偌大的院子里只我们两人,静静地,默默地,傻傻地等着。
妹妹把发辫松开,又编上,编上,又松开。我看着妹妹,想起她已经快长成个少女了,呆痴了好一会。忽然又清醒过来,赶紧回到屋里,往炉子里又添了几根新柴。
再比如说我和妹妹共同去泉里挑水的事吧。
那时大姐和二姐都出嫁了。妹妹仍在新堡乡九年制学校上初一,而我,则跟着父亲在县城里上高二。暑假到了,我就回到家,陪着母亲和妹子,也休闲,也干活。
在有关杨庄的传说里,有这么一个说法,在那个人类的想象力无比发达的时代,杨家的某一个祖先曾经把山顶的月亮想象成猪尿泡,并且坚持认为,那是一个白胡子的老神仙把猪尿泡吹大后用一根细细的绳子给拴起来的。
在双江河畔的一眼清泉里,我和妹子把水里的月亮捞起来,用水桶挑回去。
我已经十七岁了,妹子十三岁了,但我们还像两个永远也长不大的孩子,喜欢在月亮下挑水,喜欢把泉水一瓢一瓢舀进桶里的那种感觉,似乎只有这样,流逝的时光才会一点一点地回来。
一路上,到处是野花淡淡的清香,万物骚动不安,我们身披薄薄的白光,像披着一件纱衣。
我们把水倒进缸里,月亮就消失了,我们都怀疑它已经化成了水,在水里游弋。我们站在院子里,那遥远时代的月亮又出现了,真的像猪尿泡那样悬浮在山顶,我们只要骑上它就能够远离尘世。
这时候,杜鹃会叫起来,高一声低一声,深一声浅一声,仿佛在召唤走失的魂魄,又仿佛在唤醒记忆的种子。
西藏画家德珍作品《我的姐妹》做裁缝的女孩妹妹心中的苦涩,使我想起一个做裁缝的女孩来。
我上高三那年,因为学习成绩不太理想,母亲断定我不会考上大学,就做出了找寻儿媳的打算。
母亲喜欢的那个女孩,住在洮河边那个名叫木耳的小镇上,开了个裁缝店。我放假回家的时候,有时会看到一两个男孩在她店里闲坐,聊天,嘻嘻哈哈的。有时只看到她一人,停了手中的活,朝着窗外发呆。
母亲一直渴望她能做自己的儿媳,她叫妹妹给我写信。妹妹喜欢恶作剧,把母亲的意思表达清楚后,总是用竹笔蘸些墨水,画出蓝色的天空,碧色的河流,和青葱的森林。森林旁,孤然静卧着一座新兴的小镇。小镇里,一根木杆挑起一面绿色小旗,旗上写着三个黄色汉字:裁缝店。
但我不喜欢那个女孩,她在店里嘻嘻哈哈或傻傻发呆的模样,都让人觉得很不舒服。
所以当母亲托人带我到女孩家相亲的时候,我还是没有踏入她的家门,只让媒人一人去试探究竟。媒人后来对母亲说:“你那儿子,躲到小镇旁那条河边去了。我找到他时,他就像土司家的傻少爷,在数那些河底的游鱼呢!”
我才不愿意娶一个傻傻发呆的女孩做老婆呢!
女裁缝最终还是嫁给了别人。新婚那天,她提着裙子从楼梯上一步一步小心地走下来,恰好遇到因刚刚考上大学而意气奋发的我,就抱着伴娘的胳膊狠狠地哭了一场。
几年后见到了她,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原以为又丰满又滋润,却是黄皮寡瘦的。她看了我一眼,没认出我,挑着两桶水忽闪忽闪地走远了。那瘦瘦的背影,让人心酸。
巧合的是,那个瘦高的皮肤黝黑的小眼睛的伴娘,最终却做了我堂弟的媳妇。
母亲生前说,这件事,像一条蛇,一直躲在黑暗潮湿的往事里,动不动就会跑出来,让她伤心:“念书的人,大多都是陈世美!”
我争辩说:“那时我还没考上大学,不算陈世美!”
母亲死后,我很是内疚当时的决定。我总是记起那个女裁缝,记得她朝着窗户发呆的模样。那一年她十五岁,下午的阳光黄黄地照着木耳小镇的土街,照着屋顶上翻飞的经幡,照着女孩青春却木然的脸庞。
西藏画家德珍作品《我的姑姑》侯先生教书的侯先生,祖上是昝土司的百姓。但他不那么喜欢藏文化,对汉文化倒情有独钟。他读的是有汉字的那种书,有叫《三字经》的,有叫《三国演义》的,也有叫《老残游记》的。尤其有几本厚厚的《史记》,平时藏在箱子里,闲暇时就取出一本,把手仔细地洗净,慢慢地擦干,慢慢地翻看。
他把那《史记》看得多了,竟入了魔,认为杨庄肯定存在着可以载入史志的人。
他准备写一本《杨庄村志》,想给那些村长、喇嘛、阴阳、樵夫、船夫、画家、诗人、木匠、猎户们弄个本纪、世家、列传什么的,还说群体事件可以写成表,故事的边角废料能整成书。
我们听得稀里糊涂,不知道是该表示赞同还是该表示反对。因为他的《杨庄村志》,有缘的人见过几沓,却一直没成书。听说他还在写,断断续续的,似乎永远也写不完。
除了写《杨庄村志》,年关之际,他还喜欢给村里人家写对联,编些与村庄命运有关的句子:
上联:种麦种豆种洋芋山里人家家有余粮
下联:养牛养羊养孩子尕杨庄户户奔小康
横批:小康之路
乡亲们欢喜地来了,捧着笔墨纸砚,展开大红的纸张,看他龙飞凤舞地挥毫泼墨,都傻着一张脸,露出对汉文化格外敬畏的表情。待纸上的墨干了,才小心地叠起来,揣在怀里,欢喜地去了。
在侯先生的身上,我看到了文字的力量,也深信这力量甚至会影响村庄的命运。于是,在暗夜里,我也偷偷记下许多人的名字,也记下了与这些名字有关的故事。
西藏画家德珍作品《祈祷》喇嘛代杨庄人把有魄力有能耐的狠角色,叫脏腑客。
脏腑客喇嘛代,也是杨庄的一个人物。
喇嘛代的祖父,曾是杨土司的百姓。到喇嘛代父亲那一辈,土司制度被取缔了。但喇嘛代还是喜欢自豪地宣布:“我可是杨土司的百姓!”
喇嘛代的房前,住着汉人李阴阳。李阴阳迷信,担心财富流失,竟将房顶的水道通向了喇嘛代的院子。某年秋天,暴雨如注,李阴阳家的天水流到喇嘛代家院里,地上溅出了一口深坑。喇嘛代一气之下,把那通水的水槽给捅了下来。
李阴阳家的天水从房屋后墙上漫下来,渗透了墙身。李阴阳的儿子发现了问题,跑到喇嘛代家来看究竟。不看不知道,一看气不打一处来,当即骂喇嘛代是半番子。
半番子是杨庄一带对不会说藏话只会说汉话的藏族男人的叫法。这叫法,其实也没有什么歧视的意思。但正在气头上的喇嘛代觉得这称呼里有着鄙视的意味,恼怒之下抽出腰刀威胁对方:
“你再敢乱骂,我一刀砍了你!”
李阴阳的儿子却不害怕,冷笑一声:“你能把我的球给割了?!”
喇嘛代:“日你妈,我就要把你这尕崽娃给骟了!”
谁知李阴阳的儿子竟把脖颈伸过来说:“你敢!”
喇嘛代愣住了,不知该怎么办才好。
李阴阳的儿子说:“知道你就不是咬狼的狗,还冒充儿子娃呢!”
喇嘛代生了气,拔出半截刀,用刀背撞李阴阳儿子的脖子。谁知对方伸手一抓,抓住了刀鞘。这不抓还好,一抓,喇嘛代赶紧把刀子往怀里拉。双方用力夺刀,刀子就翻了个身。李阴阳儿子的力气大,抢得猛了,刀子就过去了,割到了自己的脖子。谁知脖子不经割,一下子就冒出血来,人就倒下了。
喇嘛代惊慌之下,逃往四川。过了六七年人不人鬼不鬼的生活后,还是没摆脱公安家的追逃,只好自首了,如今仍在服刑。
他和李阴阳的儿子,或许也会成为侯先生《杨庄村志》里的人物吧!
西藏画家德珍作品《冬季的鼓乐》李阴阳和小三郎的母亲相比,李阴阳的痛苦可能是永远无法消除的痛苦。
自从喇嘛代误杀了自己的儿子后,他痛苦了好长时间,也糊涂了好长时间。十年后的某个腊月,他的老婆因病过世了,他不哭,也不笑,埋葬了死者。可是,新年到来不久,他突然给人说:“我老婆儿子都还活着,我要找到他们。”
于是,清明那天,他开始在村子里找已经死去的老婆和儿子。
他走到路口,身边的世界是那么安静。天空里飘着些云朵。他从空中看到了儿子的笑脸,但一晃就被风给吹散了。田野里,新麦开始发芽,从土里钻出来,他看到了老婆的头发,只是碧绿的颜色。他偷偷拔了几根,手指都被染绿了。村边的双江河,倒影着天上的太阳,摇摇晃晃的,很不安静。他从水里看到儿子的眼睛,黑黑的,直视着他,仿佛有千言万语要说给他听。他俯下身,想捞起来,手指刚触及水面,两条游鱼就被惊走了。
他深入山林,在松树林里见到了老婆一闪而过的身影,在杨树林里见到了她留下的脚印,在红桦林里见到了儿子喜欢穿的赭色衣衫,在灌木丛里见到了儿子屙下的粪便。但他就是不能清晰地见到亲人的脸面,也不能把他们或淡薄或厚实的身体抱在怀里。
黄昏时,他回到家里,在石墙缝里,木材堆里,土墙后,凉晒着的衣被后……一一找寻。他找到了他们留下的大笑声、哭泣声、叹息声,甚至惊慌的逃离声,痛苦的咳嗽声,愤怒的抱怨声。他拿起了老婆的照片,看了一小会,放下了。又拿起儿子的照片看,双手颤抖着。儿子独自一人,抱着胳膊斜靠在一棵树上,面无表情,似乎把什么都看穿了。他就一直等着,看着,直到天完全黑下来,完全看不到儿子的样子,这才拉着了灯。
他做好了饭,给老婆盛了一碗,放在桌子上,又推到对面。又给儿子盛了一碗,放在桌子上,推到右手边。给他夹了一块瘦肉,搁在老婆碗里,夹了一块肥肉,搁在儿子碗里,说:吃吧,你们都喜欢吃肉,以前我们太穷,吃不到这东西,现在好了,这东西多的是,你们就多吃些。但老婆和儿子碗里的东西,却始终没有减少。他的碗里的东西,也始终没有减少。
第二天早上,我们准备出山,在村口碰到他。他面带微笑,朝着我们点头,算是打招呼。却不说话,我们也不说话。看样子,他已经找到了他想找的亲人。
太阳早就升起来了,暖暖地照着。村子里鸡鸣狗吠的,开始变得热闹起来。
他一个人站在村口,看着我们走远。我们踩着木桥过了双江河,到了东山脚下。回过头来,恍惚间看见,他曾经站立的地方,站着他的老婆和儿子。我们都擦了擦眼睛,这才看清,还是他一个人站在村口,渐渐地成了一个黑点。
西藏画家德珍作品《我家的牛》神算子阿克杨不能不说神算子阿克杨。
阿克八岁时被父母送往卓尼的某座寺院,当阿克。过了几年清平日子,吃不消了,就有逃了回来,死活不去了。
父母拿他没办法,只好随了他的性子。但年龄大了些,不能送到学校去,就只得让他学耕种,或者也去山上放牧。
阿克杨不喜欢耕种,也不喜欢放牧,只喜欢算命。
他说:“我从寺院里就学了这一手:算命!”
不过他算得真准:丢了牛的,在哪座山哪座湾里,找去,找到了!害了病的,是啥病,在何时得的,得罪了哪路神,怎样怎样赔罪,吃些什么药,嗨,好了!大媳妇不生育,招惹了哪里的送子观音,如何祷告,请谁祷告,两三年过去,嗳,怀上了!
因为算得准,人们不叫他阿克杨,叫他神算子。
神算子娶了女人,一边算命,一边过日子。两三年过去,女人的肚子却大不起来,神算子只好给自个算命。算来算去,问题都出在女人身上。于是带着女人四处拜佛求子,看病吃药,几年过去了,还是没什么效果。女人因为长期吃药,似乎中了药毒,脸色黑黄黑黄的。神算子开始嫌弃女人,夫妻俩的感情就越来越淡了。
后来,神算子有了外遇,他和因杀人而逃逸的喇嘛代的女人好上了。我在一篇名叫《阴山上的残雪》的小说中写过神算子和喇嘛代的女人偷情的情节:
“晌午还没到,村里的堂哥就使唤儿子来喊男人。男人和堂哥坐在屋檐下,有一句没一句的闲聊,间或端起酒杯,当的碰一下,仰起脖子将浑浊的青稞酒灌进肚里。兄弟俩在拉家常的过程中,顺便就把晚饭吃了。
“夜来了,慢腾腾的样子,把大片的灰黑色悄悄地装进院子里,装进房子里。灯忽然就被扯亮,男人醒悟过来:该回家了。
“本来直直地往家里走,在一棵杨树旁,男人却停了,站着撒尿。边撒尿边环顾四周,看到了树旁的一户人家,便收了家伙去推门。门开了,一个女人在屋里问:谁?男人说:我。女人哦了一声,迎了出来。扶住男人时闻到酒气,有些恼怒:喝醉了?男人反问:你啥时见我醉过?女人不说话了。
“女人有丈夫,因杀了人外逃,一直没回来。男人说:知道你一个人冷冷清清的,就想过来看看。女人笑了:你就不怕别人知道?男人嘟囔了一声:知道又能怎样?就一把抱住了女人。女人说:我迟早会被你害死的。嘴里说着,却将男人搀进了里屋。
“因为喝了酒,男人的事情办得不太顺利。从女人家里出来,又在白杨树下撒尿,只稀稀拉拉滴了几滴。收拾裤带时,听到女人关门的声音,小心翼翼的。男人低低地笑了一声。
“天幕上没了下弦月,男人的村庄就一片暗色。男人在自己家里,一时竟睡不着。这时酒已经醒了,脑子格外清醒。想起回家前的一幕,只记着邻家女人的皮肤,又绵又滑,像第一次用过的肥皂,顿时有些怅然,有些内疚,但也有着一丝淡淡的欢愉。
“厢房里又传来女人的咳嗽声,男人睡不住了,朝着窗户喊:嗳,把那药吃了吧,大夫说你的那病还没好呢!”
后来,女人听到了自己男人和喇嘛代女人的事,伤心之下,要死要活地折腾,终于和神算子离了婚。
离了婚的女人,找了个男人,不想婚后第二年,竟然生了个大胖小子。
杨庄的人这才知道,问题都出在神算子身上。
从此神算子也不算命了,却扎扎实实地去和喇嘛代的女人同住在了一起。
杨庄的人都替他捏了一把汗:喇嘛代迟早会回来,那时候,该怎么办呢?
西藏画家德珍作品《牧童之卓玛》排子客当然,喇嘛代至今还没有从监狱里出来。
当年曾和喇嘛代一起闯过江湖的排子客,也在等待的过程中慢慢地老了。
排子客,被人们看做杨庄的英雄,似乎也是能进入侯先生的《杨庄村志》的人。
排子客,只是个叫法,准确地说,就是打排子的人。
杨庄的排子客,是一群人。屈指算算,共七个,都是年轻人。
改革开放的春风一刮进杨庄,就惊醒了处在混乱状态的杨庄人。经过文革的“洗礼”后,杨庄的老人们开始持观望态度,不知道干什么才好。年轻人,转动着眼珠,一会想开铺子,一会想搞运输,一会想养牛养羊,但这些都需要钱,没钱,所有想法都是一截又一截的残梦。
终于,他们想到了一个发家致富的方法,那就是向洮河沿岸的树木发起进攻。他们行动了,三五一群腰揣利斧,黄昏时没入深林,躲避着林警,学那些夜鸟的鸣叫,传递着只他们才懂的讯息。松树、柏树、红桦,被一棵一棵砍倒,又在河边捆扎成木排。
随后,他们简单地吃些干粮,就小心翼翼地划起木排,注意着暗礁和漩涡。月光下,河面上闪着银光,像鱼儿们突然腾起的鱼鳞。早有人在出发前就煨起桑烟祈祷过了,但还是悬着心,只担心被无形的东西把生命遽然带走。
他们把木排打到下游,在一处叫西寨的地方停下来,把木料卖给那些精明的商人。随后,涌进岷县城,找到一家饭馆:
“老板,来七碗羊肉面片!”
面吃罢,又喝酒。酒叫“沱牌大曲”,五块钱一瓶,入口有些辣。吃着喝着,就醉了,醉在异域的客栈里,窗前也漂着一轮异域的明月。
在河面上漂流的时间一长,有的人被漩涡夺取性命,有的被突现的树木弄成残疾。灾难一多,他们就无助了,也警觉了,认识到自己的命运和被盗伐的树木的命运没什么两样。
这都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事了。后来,他们中的三个,有的在冬季跌入冰窟,再也没出来;有的在工地上凿挖隧道时,被埋到里头了;有的因突然的疾病离开了这个世界。
现在,活下来的四个,除喇嘛代还在服刑,其他的人一直坚守在杨庄,活在祈求只中。他们渴望下辈子还能转世为人。最不济也要转世成为飞禽,盘旋在故乡的山林,守护着先人们生活过的土地。
西藏画家德珍作品《窗前的少女》我和她和杨庄的这些男人相比,我似乎算是比较幸运的人了。
这村庄了,吃公家饭的,除了诗人观音代外,就是我了。因此,在杨庄人的眼里,我的头顶或许还罩着那么一轮光环。这轮光环可能是读书人所特有的,是种身份,也是种优越感。当年,也就是我工作后不久,在这轮光环的笼罩下,我有点犯糊涂了:我想在杨庄找一个女人,做我的老婆,我要把我的杨庄情结,通过她,留在我的生命里。
读书的时候,我看中的是邻村的李菊花,但这朵花让观音代给折走了。工作后,我瞄准了画家杨的女儿。不为别的,只为她长得像李菊花。利用假期回到杨庄的时候,我总是去找她的阿哥,实际上就想去看她一眼。
有一次,我终于逮到一个和她单独相处的机会,我壮着胆低声告诉她:“给我……当……当婆娘吧!”
她吓坏了,脸也红了,好半天不说话。
我急了:“你考虑考虑啊!”
她看着我,脸更红了,点点头。我又溜到她阿哥跟前,心跳得厉害。
过了几天,我又去他家。他父亲在,见我来了,下炕穿鞋,走了。
她的阿哥接待我。胡侃一会,她阿哥突然严肃起来,告诉我:“你给我妹子说的事,我们都知道了。我们家里人商量了一下,觉得不行!”
我的脑子里轰的一声,涨红了脸:“为啥?”
“为啥?”她阿哥说:“你念书念糊涂了吗?你俩是堂兄妹,是有血缘关系的!”
天哪,为了得到女人的爱情,我竟然忘记了辈分这个东西!
她阿哥说:“这事就到此为止,别往外说了,说出去别人笑话呢!”
然而过了半年,我偶遇画家杨的女儿时,她却瞅机会告诉我:“别说我俩是堂兄妹,就是亲兄妹,我也愿意给你当婆娘!”
她说这话时,语气里有种许诺,有着决然的勇气。
我突然觉得村庄、树木以及比树冠更高的云朵,都沐浴着一种奇异的光芒。风在倾听,流水带走讯息,草叶上的甲虫在叶面上记下此情此景。我知道自己是幸福的,同时也觉得身边的她,家里的老人,路上的过客,田地里觅食的家禽,都是那么令人爱恋的。
我长久地站在门楣下,看着她,不知说什么才好。
几年后,她又找到我说:“不能跟你在一起,我就会痛苦。”
说这话的时候,她早就嫁给了另一个村庄的另一个男人。我默不作声,像个猫头鹰蹲在村口。那个女人在我身旁凝视着我,阳光下,她显得那么美丽,那么柔弱,那么叫人怜悯。正是黄昏时分,西天的云霞红红的一片,像一块巨大的遮羞布,在山顶漂浮着。
其实我和她都知道,即使豁出下半辈子来折腾,我们之间的姻缘,也是不可能的。
我和她的故事,就像双江河的流水,在当年,这水或安静或凶猛地流淌,发出了不同的声音。属于我们的那些记忆之水,走远之后,就再也回不来了。
文章出处《散文》年第7期p4-p14,选稿人:《散文》主编汪惠仁,责编:张森。北京治疗白癜风疗效最好医院北京比较好白癜风医院